
《酋长如何掌权:史前政治经济学》,[美]蒂莫西·厄尔著,张炼译,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23年8月出版,288页,78.00元
酋邦是平等社会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也是小型社会走向扩张与集权的一步。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资源和人口的扩大管理,以及伴随而来的内外冲突,新的社会结构成为必要的协调机制。在《酋长如何掌权》这本书中,作者深入探讨了在酋邦社会中,以酋长为代表的精英群体如何通过多种策略巧妙地掌握权力,并建立了管理社群的政治体制。
然而,尽管书名聚焦于酋长的权力掌握,该书的主题实际上超越了酋邦社会的范畴,而是更广泛地讨论了有关权力生成和特定人群如何将权力制度化的种种问题。它深度挖掘了权力的本质,从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产生权力的源头谈起,探讨了不同类型的权力如何相互影响和交织,导致了各种扩张和演进路径的出现。它还研究了权力是如何被牢固确立和制度化的,进而成为国家建设的基石之一。
这本书对考古学家的最大贡献在于不再简单地将物质表象与特定社会结构直接联系起来,而是逐层剖析了物质遗存的特征以及导致其产生的权力根源。社会演进的路径并不仅仅局限于酋邦社会,不同的情境下,从平等到不平等的跃迁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但是厄尔对于权力以及掌握权力方式的解析并不因此而受限,而是对各种权力关系的研究者都会有所启发。
权力的产生
权力并非是自然产生的概念,而是从人的相互关系之中延伸而来的,由一个个体(或群体)对另一个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所产生的非暴力且非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是虚无缥缈触不可及的无形之物,而是广泛映射在物质世界之中,能够被权力关系中的人所感受和经历。权力的物质基础,是拥有权力者控制资源与技术,乃至人类活动的根本。
在本书开头对权力来源的讨论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概念是“异质化”。在酋邦社会中,人际关系、掌握关键生产资源或商品的经济能力、掌握武力和武器的军事能力,以及意识形态都可能成为权力来源。但是异质化的不仅仅是权力来源,更是权力扩张的进化路线。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作为三种主要的权力来源,没有哪一种能够脱离其他来源单独支撑起一个高度集权化的组织。真实情况是三种权力来源互相影响,互相干涉,互相依赖。三种权力本身和相互之间的互动影响都是动态变化的,也正因此,它们所形成的政治体的扩张方式也不同,有时甚至会引向政治体的崩溃。
为了阐明酋邦社会多线进化的可能性,厄尔的讨论并未满足于悬浮的理论建设,而是在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基础上,对夏威夷考爱岛、秘鲁上曼塔罗谷地和丹麦曲半岛三地的酋邦社会进行考察。三地分处气候地形资源大不相同的自然环境之中,且互相独立。因而被认为“既能展现酋邦社会中政治进程演进的一般过程,也能探究不同进化策略中所反映各自社会的独特之处”。而厄尔选取的切入角度,正是以考古学家的视角观察权力的物质基础。
在夏威夷考爱岛和秘鲁上曼塔罗谷地,灌溉农业经济的发展常被视为是集权政治的前提。由酋邦中领导者组织建设的灌溉设施能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力,因而所产生的产品足以供应农民的生活需求,同时还有剩余产品可以用于供养战士精英,或是用于举行仪式、建造纪念碑等。在这两个例子中,灌溉设施所提供的便利使得农民对其依赖性增高,被迫或自愿付出劳动或产品来交换使用设施的许可。控制了灌溉设施的酋长因而从中获取了对农民的控制权。此外,被集中于酋长手中的剩余价值又被再次投入新的灌溉设施的建设,或是用于维持军事实力,因而酋长的统治得以稳固和扩张。
但是经济发展产生剩余价值导向集权的逻辑并非是理所当然的,走在相同路径上的政治体往往会因为身处不同的环境条件中,而在发展速度、稳定性及特征上有所不同。例如在万卡时期的上曼塔罗谷地,较为破碎的地形使得大规模的灌溉农业发展受到了限制。较低的集约化程度导致可用的剩余产品较少,难以供应中央系统所需求的财政和军事实力,因而限制了政治体制的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山地地形上防卫设施易守难攻,由此而生的“山堡酋邦”体系在整体上偏于保守。酋邦即使在军事冲突中占优,也很难达成领土和经济体的扩张,因而该地区并没有产生跨地区的统一政治体。
与之相反的夏威夷考爱岛的酋邦社会,虽然群岛间也存在自然疆界,但偏向扩张性的军事行动使得优势社群能够控制更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因而酋长可以发展相对稳定的财政体系,进而实现了政治经济体系的扩张和对军事力量的控制,最终产生了跨岛屿的共同政治体和有较高权力的最高酋长。
丹麦曲半岛上酋长们对生业经济的控制则更加有限。一方面寒冷气候限制了农业设施的长时段发展,而农业恰恰是最易将人限制在固定地区的方式。另一方面,畜牧业中牲畜虽易于管理和占有,但是草场却很难像农田一样被划分区域和严格管理。所以曲半岛酋长们对基础经济的控制力甚至比上曼塔罗谷地的酋长们更差。直到青铜时代来临,金属被引入曲半岛,原料依赖进口、加工技术复杂的金属手工业才给酋长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可以施加控制的机会。通过对金属剑原料和生产技术的控制,酋长能够进而控制战争,以及借助战争掠夺牲畜、垄断牲畜出口交换。但是不稳定的经济控制加上本身是不稳定权力来源的战争,导致酋长的领导地位难以长久维持。社群中的领导者往往在战争中崛起又被背叛,收获没有能够稳定有效地投资至政治经济体系的扩展上,最终并没有建立起中央集权化的政体。
从三个相似又不同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厄尔将经济视为权力稳定和扩张的基础,缺失这一基础时,从战争中所获的权力充满了不稳定性,随时可能为新的胜利者所推翻。而缺失了军事权力的经济体,又会在冲突中沦为失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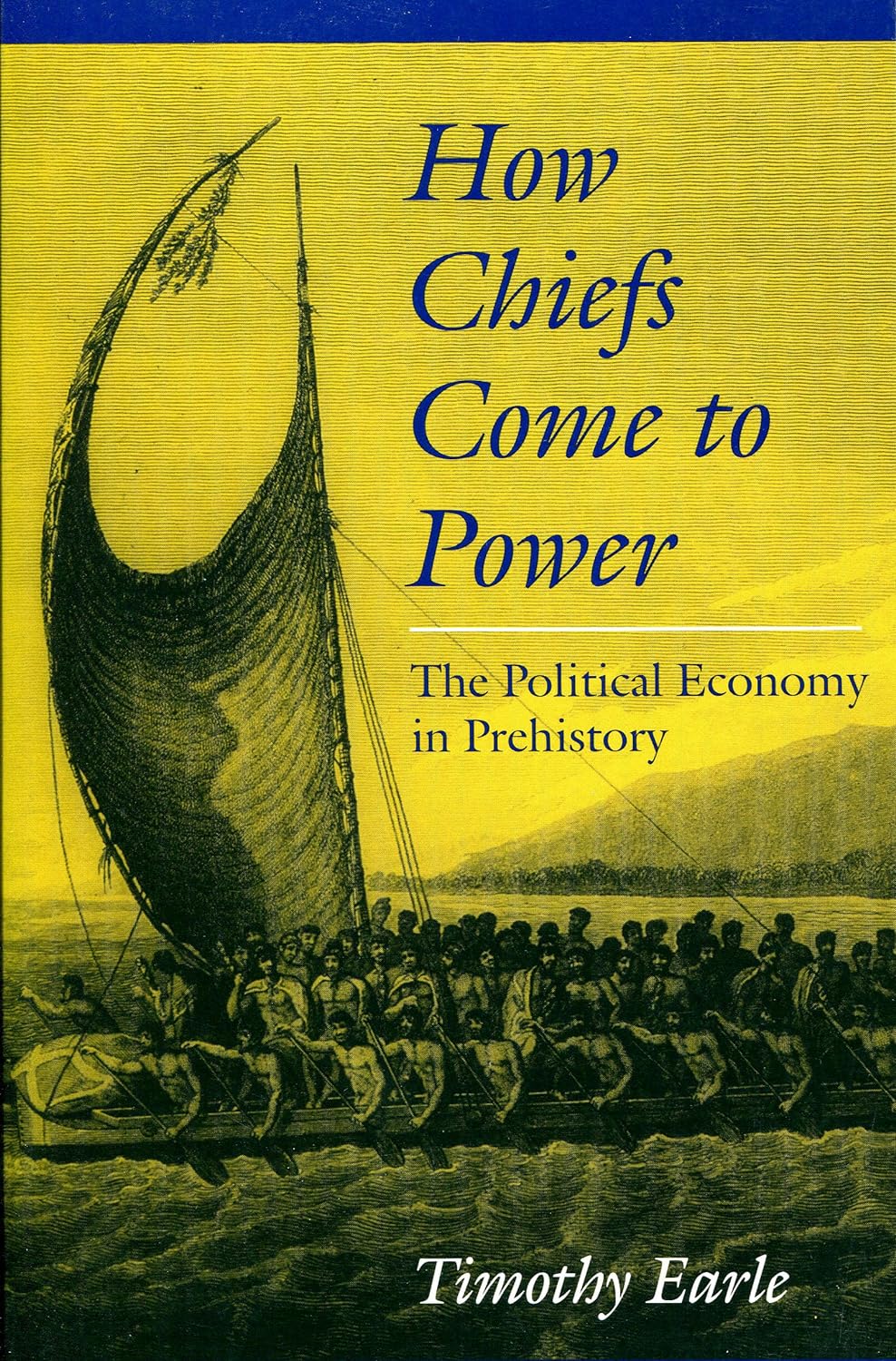
《酋长如何掌权:史前政治经济学》英文版封面
权力如何被固定和制度化
在厄尔的权力论中,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权力与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相比略有不同。他将意识形态总结为“在仪式或其他场合中被公开表现的信仰与观念系统。它由社会群体所创造,并会被其策略性地操控,以建立并维持其所具有的社会权力。其中最为重要的社会群体便是那些统治精英”。在他的叙事中,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权力似乎后于经济和军事权力而生,并且成为了将已存在的权力合理化和制度化的工具。
要解析酋邦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样要从物质角度出发。意识本身是每个人各自拥有但难以广泛共享的观念,要使得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为社群中大部分人所接受,本身就需要将意识形态表现在物质之中,然后通过社群共享的对物质世界的体验来塑造和强化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与此同时,物质化的意识形态也更易于被统治者塑造和操控。厄尔列出了意识形态物质化的三种途径:仪式活动、象征物品以及文化景观。
例如在丹麦曲半岛,战士社会时期已存在用于标识战士身份和地位的精美燧石匕首,然而由于燧石的原料与技术都未被垄断,因此其所体现的个人地位也并未高度分化,且这样的象征物品似乎并没有进一步强化个体权力或地位的功能。但到了早期青铜时代,为精英所控制的金属物品既是他们经济权力的来源,又实际上成为一种精英地位的代表物,进一步固化了他们对于生业生产和交换的控制。在纪念建筑方面,独属于酋长的土丘墓和早期农民时代属于群体的纪念碑形成了对比,同样是调动群体劳力实现的文化景观,土丘墓凸显了酋长的个人地位与对土地的占有权,而群体纪念碑则属于整个社群。
由此似乎可见,意识形态存在于权力出现之先,但唯有在权力产生且被统治者所掌控的时候,意识形态才会被统治者所用,作为强化手中权力的工具。同时意识形态也可以将已存在的权力合法化,让军事冲突中的胜利者或是新兴的精英所攫取到的权力成为制度的一部分,为整个社群所认可。
如在夏威夷群岛,酋长往往被视为神的代表,而体现他神圣性的象征物品就是材料稀有且制作复杂的羽毛斗篷。在农业活动中,酋长作为神的代表巡视群岛,主持仪式以保证农业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而在战争中,战败酋长所失去的羽毛斗篷会被献给胜利者,象征着权力的转移。通过穿戴羽毛斗篷,酋长的神圣性得以彰显,而给予或收取羽毛斗篷的过程正是将酋长权力合法化的过程。结合名为“海奥”的纪念碑、塑像等文化景观,这一为各群岛所共同认可的意识形态不断被强化和展示,成为了一套包含了宗教宇宙观、经济和军事权力体系的完备的制度。
厄尔引用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帮助解释制度化的重要性。惯习为人提供了一套结构化的社会生活,人们会按文化内共认的准则来规划行动。即使面临新的环境,人也会遵循惯习维持熟悉的生活。因而当权力被制度固定下来成为“惯习”的一部分,它就成为了社群一致认可的存在,领导者的特殊地位被默认下来,不需要再重复产生权力和取得认可的过程,也更不容易被挑战和反对。
非物质的权力
通读全书可以看出,厄尔确实受马克思主义影响颇深,将物质经济基础视为权力结构的根基。特别是在对经济权力的阐释中,控制生产资源、手工业技术、贸易路线都是统治者掌握权力的重要手段。少数人对资源与技术的控制使他们在关系中天然具有优势,这种优势可逐步扩展到对劣势个人或群体活动的控制,比如利用资源换取生产劳动力,或是在军事行动中获得服从者。而权力关系的非对称性也导致了交换往往不是绝对公平的,拥有权力者的优势会逐步扩大,并通过强化差距和制造新的差距的方式将权力稳定下来,最终形成制度化的中央集权政治体。
但是过于关注物质化的视角不禁让人反思,是否权力唯有通过物质化的形式产生,是否存在非物质来源的权力?在曲半岛的例子中,酋长通过控制金属原料和铸造工匠来控制经济权力,与此同时,作者并未提及掌握非生产类技能,比如医疗、星象、占卜等知识的人,是否能从对知识的垄断中获取权力。同样,那些熟悉社群传统,在仪式或节日中起到指导作用的人,是否也能因此在尊重传统的社群中获得权力?
此外,如前文所说,厄尔似乎将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权力作为强化和稳固经济军事权力的工具。如果超出酋邦社会这个框架,是否也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意识形态权力可以作为政治体的根本,而经济和军事权力则是强化它的工具?回想历史时期诸多宗教的崛起,往往先有宗教意识形态广泛为人所接受,后有教首从教众处获取经济或政治支持来维持教会运行,以及扩张教会。
对于仅能从物质遗存中复原古代社会面貌的考古学家,要求其讨论难以留下物质遗存的知识、传统或宗教似乎过于求全责备。但在权力的物质性已得到广泛关注的今天,非物质权力存在的可能性并不该被忽视,在理论体系中为非物质的权力留下空间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