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22期,作者:何彦霄、周天悦,原文标题:《社会学如何思考现代亚洲?专访社会学家约翰·李》,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约翰·李(John Lie)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他在韩国出生,在日本长大,高中起开始在美国接受教育。从“汉江奇迹”到K-POP,从日本族裔问题到寿司文化,从发展经济学到文化研究,他写作的切入点和视角在不停变换。
透过这些丰富的题材,除了一以贯之的怀疑、批判精神,我们也能看到两个核心的问题意识:一是对增长主义主导的发展观念的反思,他更加关注族裔、文化、传统等非政治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二是带有历史视野的思考,他对快速发生又被快速遗忘的社会变革抱有浓厚的兴趣。
这些问题意识的形成与他的成长经历,以及他接受过的人文学科训练密不可分。本次访谈通过回顾约翰·李的学术生涯中的几部重要作品,尝试串联起他开阔而多元的思想历程,展现他具有全球视野的东亚思考。
问:您在您的第一本书Han Unboun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 Korea(《打开韩国:韩国的政治经济》)中,为“汉江奇迹”提供了一种政治经济学解释。您能介绍一下写作这本书的背景吗?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在西方人眼中似乎还不那么重要。
约翰·李:这并不算是我的第一本书。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对经济学、对市场的批判的,为此我提出了“交换模式”(mode of exchange)的概念。然后我写了一本关于(1992年)洛杉矶暴乱的书,探讨韩裔美国人和非裔美国人之间的冲突。《打开韩国》是再之后写的书。
我那时对发展经济学非常感兴趣,这也是为什么我写了那篇批判市场概念的论文。但是,当时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大多是关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我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在韩国任教了一年,我当时对韩国不是那么感兴趣,但对当时能读到的研究都不太满意,因为大多数已有研究要么谈论自由市场的奇迹,要么谈论儒家伦理的伟大。因此,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其实是对当时的一些主流观念的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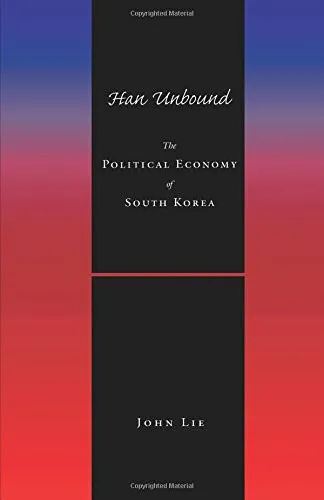
Han Unbound, John Li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问:后来您出版了Multiethnic Japan(《多族裔的日本》)和Zainichi(《在日朝鲜(韩国)人》),能谈谈您为何会转向关注日本的民族问题吗?
约翰·李:尽管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很大的影响。马克思认为真正重要的只有政治经济学,其他都是次要的。我对这个观念持批判态度,并开始对那些政治经济因素之外、同样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事物感兴趣。我对日本的研究兴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当人们讨论日本的时候,首先提到的通常是日本是世界上独特的单一民族社会,但这种观念是不对的,所以我写了《多族裔的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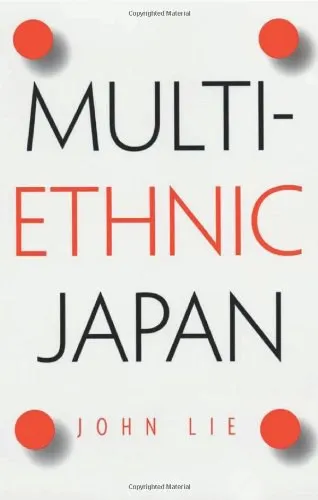
Multiethnic Japan, John Li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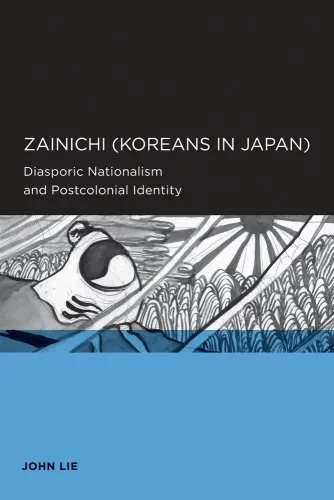
Zainichi, John Li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在日朝鲜(韩国)人》是对这一问题的延续。其中最讽刺的是,在日朝鲜(韩国)人因为不是日本人而受到歧视,但他们又生活在一个被认为没有少数族裔成员的社会中——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双重打击。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的语境中,人们一般认为是差异激发了歧视。但实际上,我认为在日朝鲜(韩国)人和日本人长得基本一样,特别是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他们的说话方式相似,看同样的电视节目——他们在文化上几乎被同化了,但即便这样,他们仍然被持续地“他者化”,以至于甚至在第四代移民之后,在日朝鲜(韩国)人仍然被看作“外国人”。你能够体会到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
问:2015年,您写了一本关于K-POP的书。当时K-POP在西方还没K-POP的书。当时K-POP在西方还没有如此受到关注,相关研究也显得没那么主流。您是怎么想到要研究K-POP的?
约翰·李:如果你在40年前甚至20年前问我,韩国会生产出伟大的智能手机吗?会生产出伟大的汽车吗?我的回答会是“也许吧”。但如果你问任何人,韩国会生产出受全球欢迎的流行音乐吗?他们的回答肯定是“不会”。所以对我来说,这个现象本身就很有趣:一件如此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同时我也认为,韩国的案例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在过去60年间的变化是如此之快,显现出一种“压缩”的特质,而这种激烈的变革在K-POP的流行中表现得最为生动。我们所知道的K-POP之外的韩国流行音乐,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因此在我看来,K-POP是一个足够有吸引力的案例,它集中展示了韩国普遍存在的“文化健忘症”,以及人为地将“传统”与“当下”割裂开来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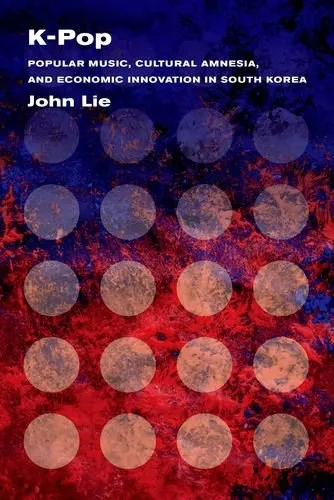
K-Pop, John Li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问:不论是从经济表现还是文化影响力来看,日本似乎已不再是东亚研究中的“热门”。您的新书Japan,the Sustainable Society(《日本,可持续社会》)为什么仍选择将日本社会作为研究对象?
约翰·李:就如同我在20世纪80年代对韩国产生兴趣一样,我的研究兴趣始终逆主流而行。更重要的原因是,尽管日本曾被认为应该是“世界第一”,但它也只是众多按西方模式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国家之一,韩国等国家按照相似的发展方式紧跟其后。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那个阶段的日本并不显得那么特别,因为它与其他国家并没有太大不同。我反倒认为现在的日本更有趣,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环境友好的、文化可持续的生活的可能性——这可能是我们未来为了存活下去所必须学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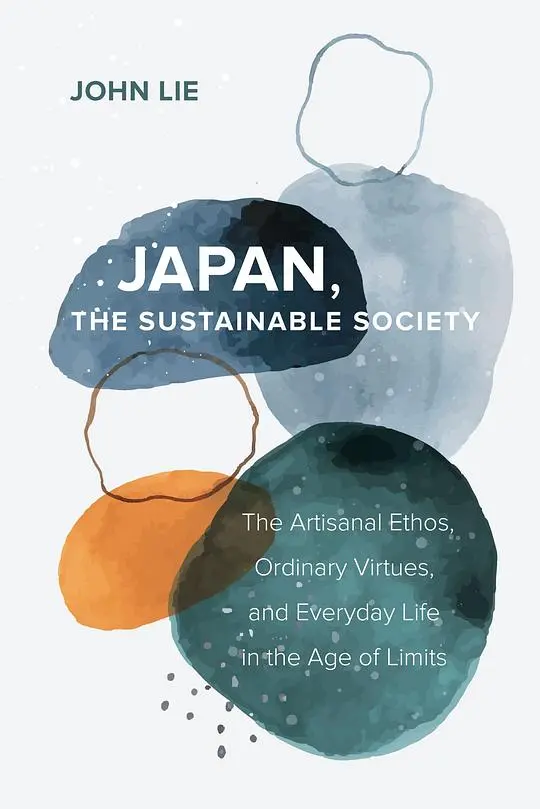
Japan, the Sustainable Society, John Li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1
问: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倾向于将经济增长看作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万能药方,或是衡量一个国家好坏的标准。您如何看待这种观念?
约翰·李: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观念,它与我们关于进步的观念密切相关。我认为在大多数文明中,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增长并不总是处在一个中心的位置。
不论是从黄金时代到黑铁时代[1],还是在中国的古典文化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关于循环或者衰退的叙事。我认为18、19世纪以来,随着大家对于进步的关注,才有了越来越多的增长主义的观念,不管是亚当·斯密,还是卡尔·马克思,经济增长成了一个基本前提、一个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事。到了20世纪,这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仰,以至于今天,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我们所设想的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都是期待更多的增长。
问:在您关于后增长时代的日本的分析中,您没有采用自上而下的视角提供传统的政治经济分析或解决方案。您为什么选择以日常生活为切入点?您特别讨论了寿司和泡温泉,是什么让您决定专注于这些文化面向?
约翰·李:当人们思考我们如今面临的主要问题时,大家很自然地会去寻找政策层面、政治经济层面的解决方案,因为大家被增长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支配,因此很难不以此为前提去寻找解决方案。我认为日本生活的某些部分还没有被这种意识形态侵蚀。它们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并展现出可持续生活的一些基本要素。

纪录片《寿司之神》(2011)海报
我给出的一个例子是寿司,但它仅仅是手工艺文化领域的一个例子。对于那些寿司匠人来说,做这行并不一定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找工作是因为想赚更多的钱、学习是因为想找一个工资更高的工作……这些观念在现代生活中很常见,但这也只是某一种生活方式而已。你试图通过练习某种手艺使自己变得更加精进、试图传承传统、在工作时获得自我满足……这些则是另一种关于“好生活”的观念。
泡温泉是我给出的另一个例子,举这个例子是因为这件事所有人都可以做到。要想成为一名大师级的工匠,不论是谁都必须付出努力和坚持,但放松并不需要花费多少努力,而休息、放松又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问:您是如何定义可持续社会的?您认为日本的案例能为其他正在经历缓慢增长的成熟工业社会提供哪些启发?
约翰·李:日本并不能算是一个特别好的案例,因为日本商界和政界的核心人物都还坚信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他们脑子里只有增长。所以我不知道日本在这方面是否能算得上做得很好。但有其他领域能够提供可供参考的方案,比如,我认为可以是寿司,可以是动漫,也可以是任何人都能享受的出色产品……它们的共性是,其目标不是增长,也不是获得更多的钱,而是提供某种可供栖居的生活。
问:东亚的人口问题,尤其是低生育率,引起了广泛关注。您如何看待人口、生育的可持续性问题?
约翰·李:我认为西方关于个人主义的观念对东亚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我并不认为一定是个体主义观念导致了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尽管理论上它们有这样的效果。我认为东亚更值得关注的地方是,我们没有什么超越性的信仰体系或价值观来维持日常生活。在东亚,人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有点空虚的,当然我并不是说西方就有多么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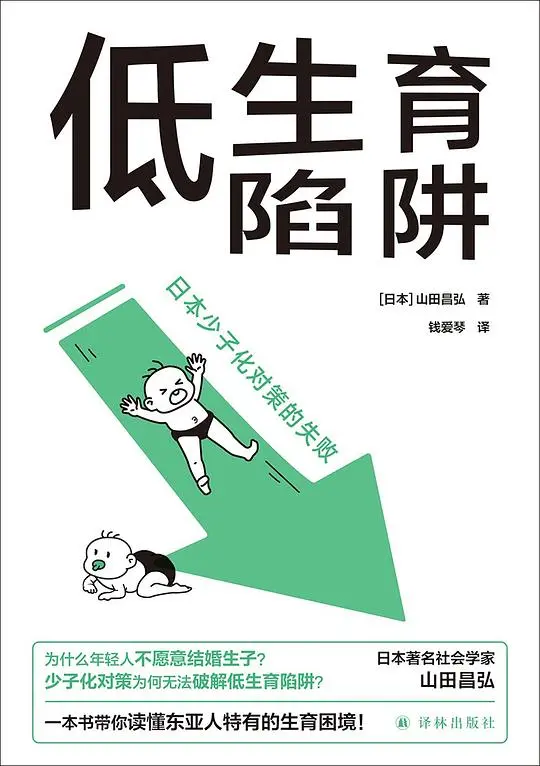
低生育陷阱,山田昌弘,译林出版社2023
至于人口问题,我其实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的人了(笑),尤其当你考虑到紧迫的环境问题时。但如果你信奉增长主义的意识形态,那么它就是一个问题;如果你相信更多的钱能解决我们关于存在的焦虑,那么它就是一个问题。但这件事本身其实并不必然构成一个问题。
问:您曾提到想要写一篇探讨20世纪初德国对日本知识界的影响的文章。我很好奇这与您平时的社会学兴趣有何关联?
约翰·李:我对人们是如何忘记他们曾经历的迅猛变革的非常感兴趣,德国对日本知识界的影响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发生在不算很久以前,这种影响在当时是如此显著,但到了现在,在短短40年的时间里,这样的影响就消失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如果你是在140年前来到日本,我们大概率会用汉字交流,甚至以传统的中国诗词交流,当时人们熟谙这些诗词中的典故,中文是日本文化界的通用语言。而如果你是在20世纪上半叶来到日本,那时人们更可能在研究德国的经典或社会理论,我们说的大概率会是德语。
所以我觉得有趣的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现在的想法其实相当奇怪:我们都认为这个以英语为主导的世界会持续存在。虽然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想讨论我们的共识变化得如此迅速,我们对过去的遗忘也是如此迅速。
问:访谈的最后,能谈谈您近期的研究计划和一些正在进行的项目吗?
约翰·李:我最近刚完成的一本书是关于全球环境危机的。我在其中想表达的是,如果我们压根没注意到一些问题,那么就不可能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这本书里我对人类的未来非常悲观,因为我觉得我们很难团结起来采取行动,当然危机本身也相当棘手。在“退休”之前我还有好几本想写的书,但问题是,我声称自己是一个社会理论家,可是我又觉得社会理论这个领域已经完蛋了(笑)。
我不太会考虑写一部社会理论的鸿篇巨著,因为我觉得没有人会去读。但这几本书中的一部分将会是关于社会理论的。另外还有一本书可能是关于日本、关于日本生活中的个人主义的。很多人认为日本是一个整体主义社会,但在我看来,它实际上可能是世界上最个体化的社会之一——这将是那本书的一个关键论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22期,作者:何彦霄、周天悦,原标题为《社会学如何思考现代亚洲?专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约翰·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