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17年,大宋天禧元年,大辽开泰六年。
这一年,大宋改元“天禧”。“禧”是吉祥、幸福的意思,“天禧”就是希望上天赐予万民吉祥、幸福。
如果你听过上一期节目,就知道为什么要改这个年号了。因为去年的一场大蝗灾,横扫了半个中国。今年一开年,朝廷就忙开了:大赦天下;老百姓过去欠的赋税,统统免了;受灾地区的田租,也不用交了;茶、盐这类生活必需品,减税降价;等等。凡是朝廷能做的,能减轻老百姓负担的事儿,今年都做了。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皇帝担心的,不仅有当前的民生疾苦,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过去9年,大中祥符年间朝廷搞的那些烧香拜神的活动,在信用上破产了。这是一个更重大的政治问题。改年号,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原来是“大中祥符”,老天爷肯定给咱们吉祥,你看,我手里有天书,有“符”为证啊。现在谦虚点儿了,就是个“天禧”,符不符的放一边吧,求老天爷给个吉祥。

“天禧”这个年号,一共用了五年。这五年,就是真宗一朝的最后阶段了。你看,我们《文明之旅》这个节目,看着一期只讲一年,慢腾腾的。但是这才开播四个多月,真宗皇帝就从一个30岁的青年,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快50岁了。一个时代就快过去了。
好,回到这一年:公元1017年,我们要关心的是一个人。这一年10月,老宰相王旦去世了。
王旦从病重到去世,其实有几个月的时间。从5月底开始,他就开始打报告辞职,但是真宗皇帝不同意。毕竟用了这么多年的宰相,舍不得啊。
拖到了8月份,王旦实在撑不住了。让两个人搀扶着,来跟皇帝辞职。真宗一看,王旦瘦得不行了,自己身体也不好,说的话就有点伤心了:“我还有大事托付给你呢,你现在这个样子,可怎么得了?”然后一抬手,把儿子叫过来,就是后来的宋仁宗,这个时候还是个小孩呢,刚7岁,让他给王旦磕头。王旦这个时候走路都要人搀着,但还是起身颤巍巍地躲,孩子就追着他磕头。你要是当时在场,旁观这个场景,在一片忙乱之中,也能体会到一种悲凉,这君臣二人,真说不好是谁在给谁托付后事。
到了10月,王旦去世,享年60岁。真宗皇帝这个时候也快50岁的人了,当了20年的皇帝了,还亲自给王旦熬药,去登门看望,王旦死后,朝廷也给了极高的荣誉。别的不说,就这个谥号,给了一个“文贞”。
“文贞”这个谥号,可不得了,是中国古代一个文臣能够得到的最顶级的谥号。“文贞”后来因为避宋仁宗赵祯的名讳,改成了“文正”。你看历史上的“文正公”都有谁?范仲淹、司马光、曾国藩,等等,要不是公认的文臣典范,或者是跟皇帝本人有特殊的机缘,很难得到这个谥号的。
不仅如此,宋朝人对王旦的评价也极高。仁宗继位以后,朝廷还让王旦配享真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朝廷在太庙祭祀真宗的时候,也得顺道祭祀一下王旦。这对于一个大臣来说,是非常崇高的荣誉。历史上配享真宗的文臣总共就两个人,一个是李沆,一个是王旦,都是我们节目专门介绍过的人,其他人像宰相吕端、寇准呀,都还不够资格。再后来,仁宗还亲自给王旦的神道碑,也就是立在王旦墓前记载生平事迹的石碑,题了一个碑额,叫“全德元老之碑”,把王旦尊称为道德上完美无缺的元老重臣。
你看,一个当臣子的,到了这个份儿上,就算是到头儿了。朝廷能给的荣誉和宠爱,真的是全给了。但是你不觉得奇怪吗?除了专门研究宋史的人,或者资深的历史爱好者,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王旦。
那这里就有问题了,王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宰相?为什么他在后世的存在感这么低呢?
好,咱们就带着这两个问题,一起穿越回公元1017年,大宋天禧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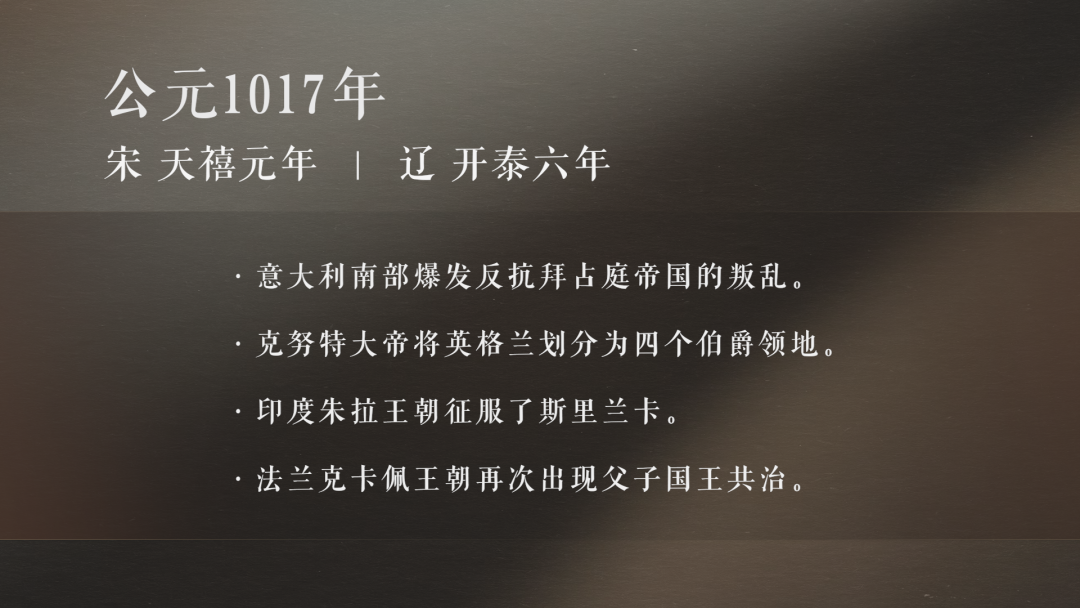
时代的王旦
这一期,我们来聊宰相王旦。
王旦是大名府莘县人,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聊城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的进士。我们在公元1015年聊寇准的时候,就说过,这一科的进士可了不得,总共出了四个宰相,李沆、向敏中、寇准、王旦。
王旦在这四个人中,是最后一个做宰相的。但是他竟然一口气干了12年。一算账,比其他三个进士同年宰相都要干得长。再一算账,他比真宗一朝前面七任宰相加起来的时间都要长。再一细算账,不得了,王旦破了一项纪录,他是北宋167年的历史上不间断做宰相时间最长的人,没有之一。你注意我的定语,不间断,对,如果是干几年歇几年,宋代初年的宰相赵普,断断续续做宰相比王旦要长。从中国古代有宰相制度开始算起,这都是非常少见的。
你看看,一个有这样出色成绩的人,居然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是不是挺奇怪的?
王旦这辈子的成就,我们得分三步来看。
第一步,其实跟他自己关系不大,就是时代给了他这样的机遇。
前面说过,王旦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的进士。这一科进士,总共录取了多少人呢?119个人。如果按成绩做区分,甲科是23个人,乙科是96个人。王旦是乙科进士,那你算算,他的成绩至少是排在23名以后。这个名次,放在隋唐五代、甚至是宋太祖时期,是很难考中进士的。因为当时录取人数很少,一般就十来个。
你看,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王旦其实是踩中了风口,撞上了大运。他赶上了宋太宗要搞“崇文抑武”的时代红利。这个背景,你可以去看我们1015年讲寇准的那期节目,那里交待得比较详细。总之,是因为科举扩招,王旦才中了进士,当上了官儿。
顺便说一句,考场和战场,看起来是两回事。但其实如果你真的站在历史现场,会发现考场和战场之间息息相关。举个例子,就在王旦的前一科,978年,太平兴国3年,皇帝主持的殿试,议论文的题目叫啥?叫《登讲武台观习战论》。咱们都不用仔细审题,乍一听就知道这篇文章往什么方向写嘛。肯定是:国家怎么整军经武,怎么战场得胜,顺便夸一下皇帝怎么英明神武、运筹帷幄。
果然,第二年,宋太宗就北伐了。出兵打仗之前,在科举殿试里面出这道题,你顺着皇帝的意思答,考中的概率当然就高。
但是,这场战争的前半段虽然成功灭了北汉,但是后来想捎带手拿回幽云十六州,却是惨败。宋太宗,腿部中箭,因为没法骑马了,好不容易从老百姓那儿找了一辆驴车,才仓惶逃回开封。
那你想,转年过去,就是王旦这一科的科举,殿试议论文题目是:《文武孰为先》——国家应该先讲求文治呢?还是先讲求武功呢?
你要是那年的考生,你怎么答?你要是再写什么整军经武,什么皇帝英明神武,你不就是打皇帝的脸吗?你当然得顺着皇帝的意思说:武力这种事不重要,治理国家,应该讲究文治。
理解了这个微妙的转变,你也就知道了,为什么王旦这样的书生的时代来了。这是王旦上升之路的第一个阶段,纯粹是时代给机会。
但是天下书生多了,中进士的也多了,为什么王旦能蹭蹭蹭地往上走,一直当到宰相呢?这就要说到他的第二步了。
第二步也不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努力,而是从他的父亲就开始编织的那个关系网。
王旦的父亲叫王祜,他在宋太祖的时候就做到了知制诰,就是皇帝的秘书,负责起草圣旨的。这个官儿谈不上多大,但是因为离皇帝近,非常容易被皇帝赏识,更重要的是,其他官员会非常小心翼翼地和这种天子近臣搞好关系。
这个王祜也确实是长袖善舞,好朋友的名单很长,其中有开国功臣宰相赵普,有后来做了宰相的毕士安、吕端。而且他还主持过好几次科举考试,提拔了很多门生。当然更更重要的是,他在太祖的时代就和宋太宗搞好了关系。那你想,在宋太宗的时代,这么个人的儿子考中了进士,仕途能不顺吗?
举个例子,王旦中进士之后,起步是在平江做知县,就在今天的湖南岳阳。县官没当几年,就找了个老丈人。老丈人叫赵昌言。这位赵昌言自己的官没多大,也就是一个转运使,地方上的一个管财政的干部,但是身后的关系网深不可测。赵昌言的父亲,在宋太宗还没当皇帝的时候就跟着太宗;赵昌言的舅舅石熙载是宋太宗的铁杆亲信;赵昌言本人是太平兴国三年进士的第三名。
那这样一个人为什么看中王旦,非要找他做女婿呢?史书上的记载,是因为他看到王旦把这个平江县治理得好,一高兴就收他当了女婿。但是你想也想得到,怎么可能这么简单?看中这个女婿,当然是因为看中了他背后的家庭和整个家庭关系网络。
所以你看,网络这个事,不是因为你跟谁谁谁关系好,所以有事就能找人办,有人帮你徇私舞弊。不是这么简单。你有一张网,而且在经营这张网,那其他有网络,且在经营网络的人,就会默默地过来跟你强强联合。所谓网络效应,就是越用越强,越经营越大。
所以不用着急,王旦在长大,他身后的那个网络也在长大。他980年中进士,11年之后,公元991年,他当上了知制诰,来到了皇帝身边工作,这是关键的一步。又过了10年,王旦终于当上了参知政事,副宰相,升到了大宋官僚集团的最高层。又过了5年,王旦正式拜相,成为大宋朝的文官领袖,宰相。这样的晋升之路,虽然不算快,但是和后来的范仲淹那种从草根做起,一路逆天改命的狠角色相比,还是显得有点得来全不费工夫,或者说,显得有些平庸了。
那你说,这里面有没有王旦自己努力的因素呢?当然有了。
《宋史》用了一个词来描述当宰相之前的王旦,叫作“时论美之”,大家都觉得王旦这小伙子不错,很厉害。当时有一个会相面的官员就说,王旦一看就是当宰相的料。就连科举同年、先一步做宰相的李沆,也很推崇王旦,说他是能担当天下大任的人。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皇帝的态度。有一次王旦见完皇帝,往外走,真宗目送他离开,望着他的背影说,将来为这个国家造就太平盛世的人,一定是他。有人跟真宗推荐王旦,真宗说,我心里早就有他了。
你看看你看看,这么整齐的好评大合唱,当然是王旦背后那张关系网慢慢发酵的效果,但是如果王旦不是一个看起来沉稳持重、才思敏捷、堪当大任的人,怎么可能会是这样的结果?
所以,公元1006年,王旦代替寇准,登上了宰相位置。那真是因缘际会啊,得到各个方面的祝福和接受啊。
但是,王旦这辈子最大的传奇不是当上了宰相,而是连当12年,成了北宋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宰相。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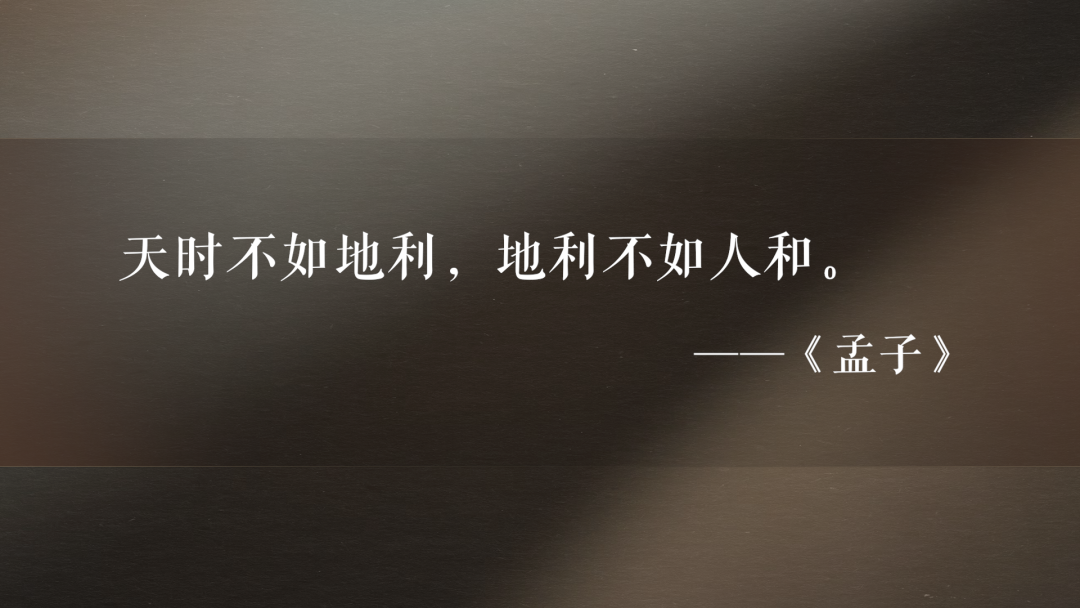
王旦的本事
要按《宋史》的说法呢,王旦这叫天生宰相命。
比如,《宋史·王旦传》里面记载,王旦爸爸曾经院子里种了三棵槐树,然后很自信地预言了一下:“我的后人呀,一定有做到三公的,种这么三棵槐树,就是为了做个见证。”
而且,按《宋史》的说法,王旦要当宰相,不光他爸爸有预感,鬼也预先知道。话说,王旦在平江当县官的时候,衙门里原来闹鬼,但是王旦来当知县了,有人听见鬼说,“宰相来了,咱们躲躲呗?”然后就不闹鬼了。你听听,鬼说的,可不是县官来了,而是宰相来了。
对,这就是正史里的记载,你说能信吗?这跟书上说,某皇帝出生的时候,满屋子红光,是差不多的意思,应该都是后人的附会。
那王旦当宰相,而且一当就是12年,不靠命,是靠什么呢?靠圣贤人格吗?表面看,正史是这么写的。
但是,《宋史·王旦传》的材料,很多来自于王旦小儿子王素写的一个介绍王旦的材料。那你想,儿子写父亲,肯定是各种溢美之词啊。
不过,如果我们把《宋史·王旦传》里的,说他怎么廉洁,怎么能干,怎么公正的这些部分,所有道德表扬的部分,都拿掉,我就会发现,这个王旦做事有一种非常奇特的风格。这种风格,值得我们仔细琢磨琢磨。
我举个例子,你先感受一下:
就在两年前,1015年,寇准刚刚回到朝廷当枢密使,就是军事部门首长,眼瞅着官儿又要丢了。寇准就跑去找王旦,说,枢密使不干就不干吧,能不能给我一个“使相”的官儿?啥意思?就是做节度使,同时加一个虚的宰相头衔。实惠也有,荣誉也有,有里有面儿的。王旦可是寇准的同年,而且一直向真宗皇帝推荐寇准,按说交情是够的,但是王旦二话没说,就拒绝了寇准:使相这样尊贵的官职,不是能张嘴要的。我这个人,不受私人的请托,免开尊口吧。
寇准当时非常不爽。不过,后来任命一下来,朝廷真给了寇准一个使相的官职:既是虚衔的节度使,又是虚衔的宰相。寇准一看,愿望实现了,既然是王旦不肯让自己满意,那想必是真宗皇帝赏识自己呗?就跑去谢真宗皇帝。真宗说,这是王旦推荐你当这个官儿的。寇准一下子就羞愧了,说我不如王旦啊。
这种事情,王旦没少干。真宗去世后,朝廷安排人修真宗朝的史书,翻出来大量的王旦推荐大臣的奏章,但在当时,没人知道这些人是王旦推荐的。听了这个故事,你可能会觉得,这有啥呢?往好了说,就是王旦做了好事不留名;往坏了说,就是王旦这人狡猾啊,人情自己不做,而是要留给皇帝做,他不过就是一个官场厚黑学掌握得比较好的人而已。
没有这么简单。
如果说,不拿朝廷的官位去做人情,把一切雷霆雨露都归功于皇帝,这个还比较容易做到的话,那下面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你再体会体会。做到这一条,就难喽。
就在前一年,1016年,朝廷新提拔了一个人当参知政事,副宰相。这个人我们以前曾经提到过,就是连中三元的状元王曾。王曾年轻啊,又新官上任,很有锐气,虽然自己当上副宰相,肯定有王旦的因素在,但他不管那个,上任之后,马上就抓住了王旦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可不小。王曾发现,王旦在处理政务的时候,经常不请示皇上,自己就拿主意做决定,而且还批上“奉圣旨”这几个字,表示这是皇帝的意思。这还得了?王曾就说,你这可不行,这不是假传圣旨吗?王旦一听,马上道歉,罪过罪过,我错了。
那你想,这是实锤啊,王曾能善罢甘休吗?他就找了一个王旦不在场的机会,向真宗皇帝打小报告。真宗就问啊,王旦这些事做得公正吗?王曾说,公正确实公正,但毕竟是假传圣旨啊。
真宗说,根据我这么多年的观察,王旦这个人连一头发丝儿的私心都没有。而且,小事不用请示,他自己拿主意就行,这是我给他的特权。你们几个要听他的话。
你听出来了吧?王旦明明得到了皇帝的授权,但是当王曾冤枉他,指责他的时候,他完全不辩解。皇帝私下给我的授权,皇帝不对你们说,我是不会说的。这个王旦也太沉得住气了吧?
你看,这两个故事:一个是,好名声我不往身上揽,一个是,坏名声我也不往外面推,你们爱怎么想怎么想,反正我就是这样。
你要是皇帝,你是不是也喜欢这样的大臣?确实,这样的事儿越多,真宗皇帝对王旦就越信任。王旦说什么,真宗信什么,就算是其他宰相、大臣讨论个什么事儿,真宗也一定多问一句:“这事儿王旦怎么看?”事情不论大小,都得等王旦说了话,发表了意见以后,才能定下来。
刚开始,我从这些故事里,能看到王旦的忍辱负重,自我承担,很佩服,但是与此同时,也觉得这么活着,实在憋屈,为了皇帝的好印象,自己活成了一个受气包。
但是有一天,我再读这些故事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感悟,换了一个角度,看到了另外一个王旦。一拍大腿,心里暗道了一声“佩服”!我把这个角度说出来,你听听有没有道理。
王旦作为一名宰相,他把什么是自己的权力和责任,什么是对方的权力和责任,以及不同场合下、不同角色之间,这种权力和责任的转换,分得清清楚楚。
比如,在前面说的那个故事里,寇准找王旦来要官当。你寇准有这个权力要官儿当吗?没有。我有权力答应你的要求吗?也没有。所以,我一口回绝。但是场合一变,面对真宗皇帝,我王旦有义务建议最合理的处理方式。那我觉得,寇准这样的人,虽然官可以撸了,但是面子还是要给,给个节度使,再加上一个虚衔的宰相,是合适的处理办法。
你看,王旦这么做,刚开始说不行,后来又说行,看起来是矛盾的,是前后不一的。但其实,他的逻辑是一以贯之的,在什么角色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再来看另外一个故事,王曾指责王旦假传圣旨。他该不该这么怀疑,这么指责呢?该啊。他看到的就是这个事实啊。那我就该道歉就道歉。那我王旦能不能把得到皇帝授权这事告诉王曾,洗刷自己的冤枉呢?不该啊。因为皇帝授权我处理事儿,但是没有授权我把这个授权告诉你们,所以,我不会说的。至于皇帝是不是告诉你们,那是你们和皇帝之间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
你感受到没有,王旦并不是天生宰相命,但他用了一种我们很不熟悉的方式当宰相。他像是一块铁板,挡在自己的每一个角色和角色之间,也挡在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之间,甚至是挡在每一个场景和每一个场景之间,针扎不漏,水泼不进。我在这个角色里,在这个场景下,面对这个人,我只判断这个情况下,怎么做是正当的。其他的考虑,我看不见,也管不着。
这叫什么?对现代心理学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叫“课题分离”。两位日本心理学家在这本《被讨厌的勇气》里面,第一次把这个概念清晰地提了出来。
什么是“课题分离”?两句话就能说清楚。
第一句话,你操心你的事,我操心我的事。别裹在一起想。
第二句话,怎么分辨什么是你的事,什么是我的事?谁承担这件事的后果,就是谁的事。
举个例子,比如有朋友借了我的钱,到期了,还是不还,我该催他吗?不催,我怕受损失,催了,我又怕朋友不高兴,你看,两头为难。那怎么办呢?课题分离啊。我的课题是,得把钱要回来,因为钱没了,后果是我承担的,所以这是我的事。那朋友不高兴怎么办?他不高兴,这是他要承担后果的事儿,所以这是他的课题,我不管。
再举一个例子,我想上台表演,但是又怕观众失望,很纠结。课题分离啊。我想上台,那就认真准备,好好表演,这是我的课题。如果我演砸了,观众失望了,恩,那是他的课题,他得处理自己的失望的情绪。
乍一听,这个课题分离好像很残酷,怎么能不管别人的情绪呢?但是按照课题分离的原则,这是两件事。我催了朋友还钱,避免了我受到钱财的损失,这是一件事。我朋友因此不高兴,我还想挽回我们的友谊,那是另一件事。分开处理,先处理钱的事,再处理友谊的事儿。别裹在一起想。
对,很多人间烦恼,都是因为把别人的事和自己的事,把自己的两件不同的事儿裹在一起想,越想越乱。
想到这儿,我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王旦之所以能当12年宰相,跟他的这个“课题分离”的能力可能很有关系:一码是一码,该怎样就怎样。片刻不乱,丝毫不爽。用这样的方式,他这个宰相当得没有任何软肋和破绽。
只有搞懂了课题分离这个概念,而且认可王旦有这个强悍的能力,我们才能看懂王旦有些做法。
比如,就在1017这一年,真宗皇帝让王旦推荐继任宰相的人选。王旦说,我推荐寇准。真宗说,得了吧,寇准这个人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又刚又倔,你再说个别的人试试?王旦说,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我身体不好,待不住,告辞了。后来果然,王旦死后,真宗还是不得不启用了寇准。
你问我,谁合适接班,我认为寇准最合适。这是我的看法,我的责任,我的课题。皇帝您觉得,寇准脾气不好,您不舒服,那是您的课题,您自己想办法消化。
再比如,王旦当宰相,是负有为朝廷推荐人才的责任的。那他怎么推荐呢?如果他听说某个人不错,他会在几个月之后,找机会跟这个人见一面,聊聊天,考察他一下。哎,奇怪,宰相不是求才若渴吗?应该马上就办啊?为什么要过几个月呢?因为,有人当着我面说某个人不错,我不能让他觉得,这是他的美言起了作用。隔了几个月,就谁都不知道,我是为什么要找这个人聊天了。所以,任何人当着我面表扬任何人,他心里都没底,这话我是不是听进去了。
在聊天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人确实有才能,就向皇上举荐。但是这些被举荐人,再想见王旦一面,抱歉,不见。道理也很简单,我跟你聊天,是为了发现人才。这是我的事,我该做的。你现在回来找我见面,是看见机会了,想往上爬,或者想感谢我,这是你的事,是不应该做的。所以,对不起,我不配合。
你想想看,这是一种多么强悍的意志力。看过那么多古人的传记,我特别惊讶的是,王旦,一个1000年前的宋朝人,竟然为现代心理学里的“课题分离”原则,提供了那么精彩,那么彻底的案例。
当然了,王旦这种“课题分离”的本事,很可能是性格使然。人类文明要到工业时代,才发展出所谓的专业主义,也就是在组织运行中,排除人格化因素。像王旦这样的行事作风,会发展成一种普遍的职业伦理。这是后话了,咱们以后遇到再展开。
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分清了你的事和我的事,我不管你怎么想了,那我就能按着我的性子为所欲为了吗?也不行。
那王旦又是怎么做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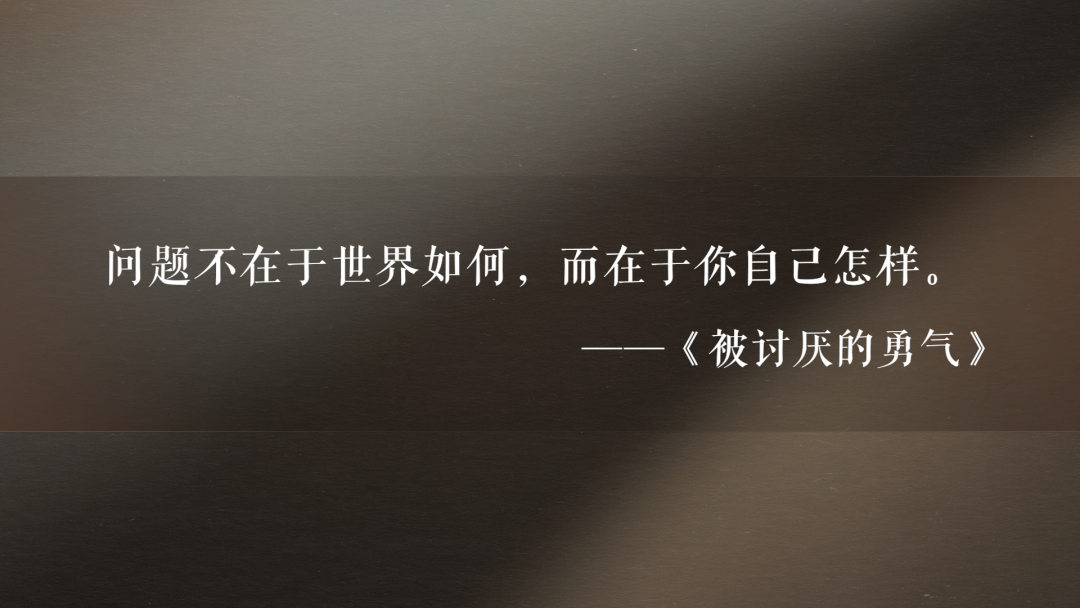
该怎样,就怎样
我越看和王旦相关的史料,就越觉得不可思议:这个王旦,他不但把别人的课题和自己的课题分得清清楚楚,而且在完成自己课题的时候,几乎每一件事,都做在点儿上过。这又是怎么做到的?
晚清和民国时候的书里面,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叫“正办”。正确的“正”,办法的“办”。什么是“正办”?就是这个事,最正大光明、最理该如此的处理方法,就是“正办”。这个用法,我们现在的汉语里是没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词的语感特别好,特别能帮助我们在纠结的时候,它一出现,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世界的本来面目。
举一个近代史上的例子。有本书叫《庚子西狩丛谈》,里面提到了一个李鸿章和曾国藩的故事,这是李鸿章亲口对这本书的作者讲的。
话说,李鸿章要接手曾国藩办洋务,就是和洋人打交道。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看起来,洋人是个大麻烦,既不能得罪,因为打不过,又不能屈服,因为对舆论不好交代。为难吧?曾国藩就问李鸿章,你打算怎么干呢?李鸿章说,我就跟他打“痞子腔”。这是安徽话,意思是跟他油腔滑调。既然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油滑一点总没错吧?万一滑过去了呢?
曾国藩说,不对。依我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一个“诚”字,诚恳的诚字。洋人,我们打不过,也搞不清楚他是怎么想的,那就老老实实,以诚相待。曾国藩下面讲了一句至理名言,他说,”以诚相待,虽然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过于吃亏啊。”李鸿章回忆说,后来这一辈子和洋人打交道,就多亏了老师曾国藩的这一番提醒。
你看,这就是所谓“正办”的精神。我搞不清楚情况,没关系,我有正大光明、本来如此的应对方法,虽然占不到便宜,但也不至于破了底线,吃了大亏。
比如,有一个真相,我承认了吧,要承担损失,不承认吧,又于心有愧。很多人这个时候就纠结了。那这个时候的“正办”是什么?先承认啊,先问心无愧,然后出现了损失,想办法弥补、挽回损失啊。这才是“正办”。
你可能觉得,不对啊,真宗大搞天书封禅、东封西祀,王旦不也该支持支持,该配合配合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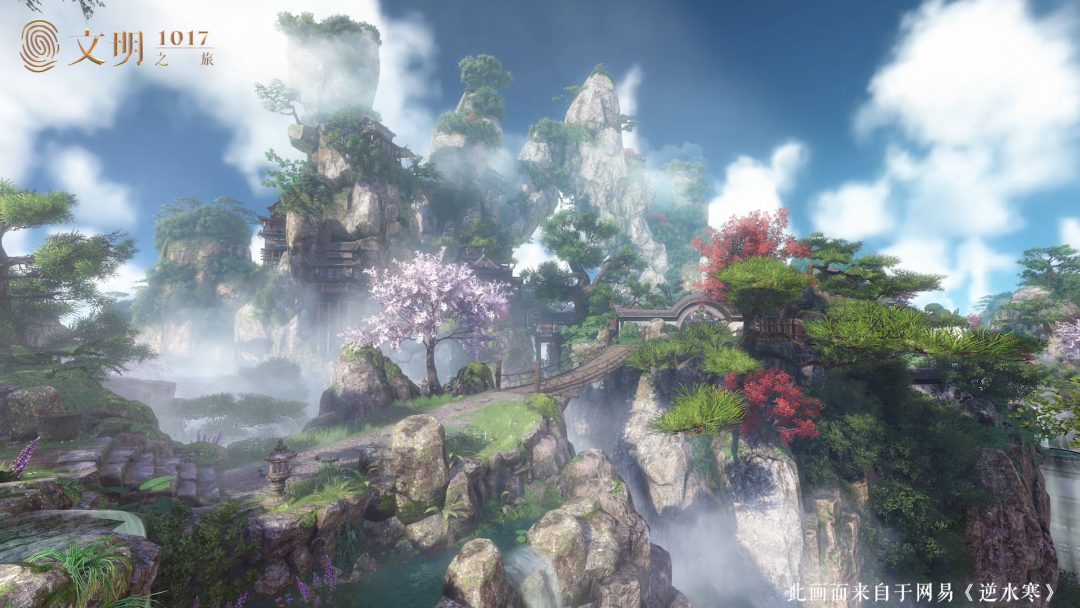
但仔细分辨王旦支持和配合的地方,都是宰相的职责所在,他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心里还是知道,那只是神道设教。让我当天书使,每次举行大典,行礼如仪是可以的,但是,对不起,不高兴,我还是挂在脸上的。
有一回,真宗组织大臣观看祥瑞图,王旦就表示,我汇报工作,上报祥瑞的情况,可不是我自己亲眼看见的,都是照着有关部门的报告说的,希望史官这个事记下来。
更绝的是,有个支持真宗搞迷信的人上书,文件流转到王旦这儿,王旦猜测,不过是报告祥瑞谋个升官提拔,他就能闭着眼睛把文件封上,坚决不看。
这种正办的行事方法,一直坚持到王旦生命的最后一刻。你还记得我们这期节目开头的时候讲,王旦病重,临终前,真宗皇帝又是登门看望,又是亲自熬药,还赏赐了五千两白银。
但这仍然只是皇帝你的课题,你怎么对待合作了12年的宰相,是你的事。而我自己的课题是,要反省自己没有及时劝谏停下那场天书封禅的闹剧。
于是,王旦在临死前,非常决绝地留下遗言,要剃光头发,穿着和尚的黑色僧衣入葬。要知道,丧礼是传统宗法秩序的重要一环,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以僧人的方式入葬,是非常惊世骇俗的。但对于王旦来说,该怎样,就怎样,我不会因为感念皇恩,就把自己没有按住天书封禅的事给糊弄过去。别的做不了了,我总可以安排我以什么方式入葬,以什么方式离开吧。
人很多时候会面对左右两难、局面混沌的情况,这个时候,“正办”两个字会帮特别大的忙。
古今中外的做人智慧,这都是一个很高的段位。我听过一个西方的寓言故事,也有类似的精神。
说有一个人死后,接受基督教所谓的审判。他进到法庭一看,审判官是大天使加百列,证人席上呢,坐着一个老头儿。审判官每宣读他的一条罪状,那个老头儿就赶紧站起来为他辩护。比如,“他虽然杀人了,但是他是为了保护他的妹妹啊,情有可原的”。最后,这个人还是被判,要下地狱。这人对这个审判结果并不意外,但是他好奇啊,这个老头儿是谁啊?萍水相逢的,为啥要为自己辩护呢?就上去问,你谁啊?老头儿说,我是上帝啊?啊?上帝?那你为什么不做审判官呢?上帝说,如果我来做审判官,那天下就没有罪人了,就没有人下地狱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非常震撼。
我们经常被困扰,我到底是应该坚持原则呢?还是应该得饶人处且饶人呢?尤其是手里有点权力的时候,这个困扰就更大。
但是这个寓言故事,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尊重规则,但与此同时,想方设法地、竭尽全力地帮助每一个被规则难住、困住的人。
一个保安的工作责任,仅仅是拦住那些没有带入门证的人吗?还是应该一边拦住他们,一边为他想办法,帮他进去?当然是后者。我们不能只在规则和人情之间左右为难。我们应该是:面对规则,就尊重规则;面对人,就帮助人,并看到这二者其实可以并行不悖。
世界不是混沌一团的,它不过是一个又一个课题,精准识别它,一个接一个地解决它。该怎样,就怎样。这才是“正办”啊。
这是我从王旦的故事中,得到的一点启发,也供你参考。
这里是1017年,我们送别了宰相王旦。王旦在的时候,虽然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朝政毕竟波澜不惊。王旦这一走,王钦若当了宰相,然后就是各种风起云涌,跌宕沉浮,一言难尽。大宋朝的政治气氛马上就紧张了起来了。不过,现在这个阶段还只能算是山雨欲来,再过两年,那场政治上的滔天巨浪才会真正来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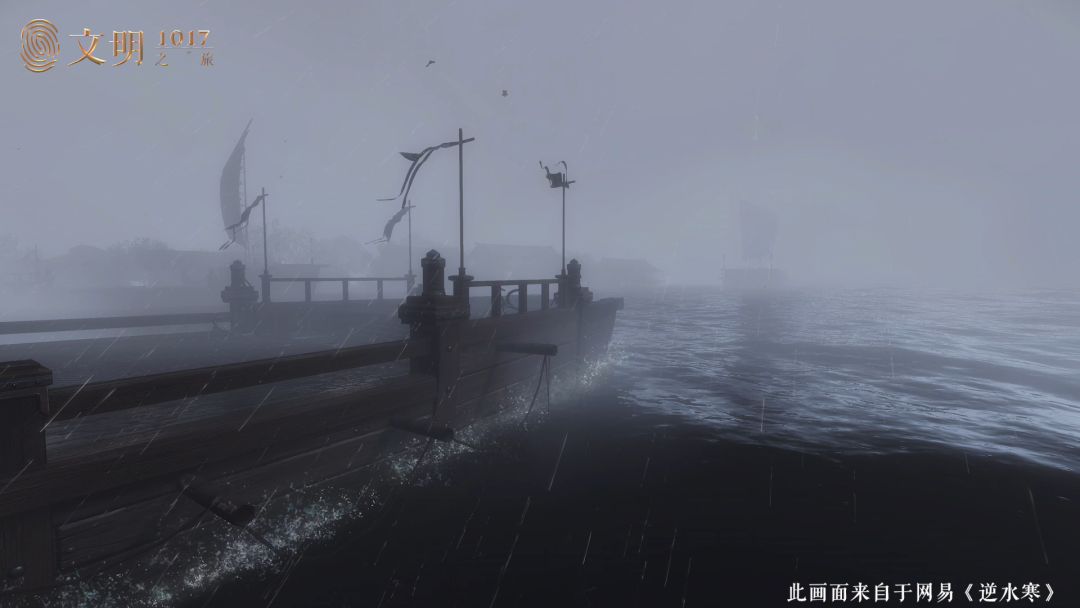
好,这就是1017年我们的话题。公元1018年,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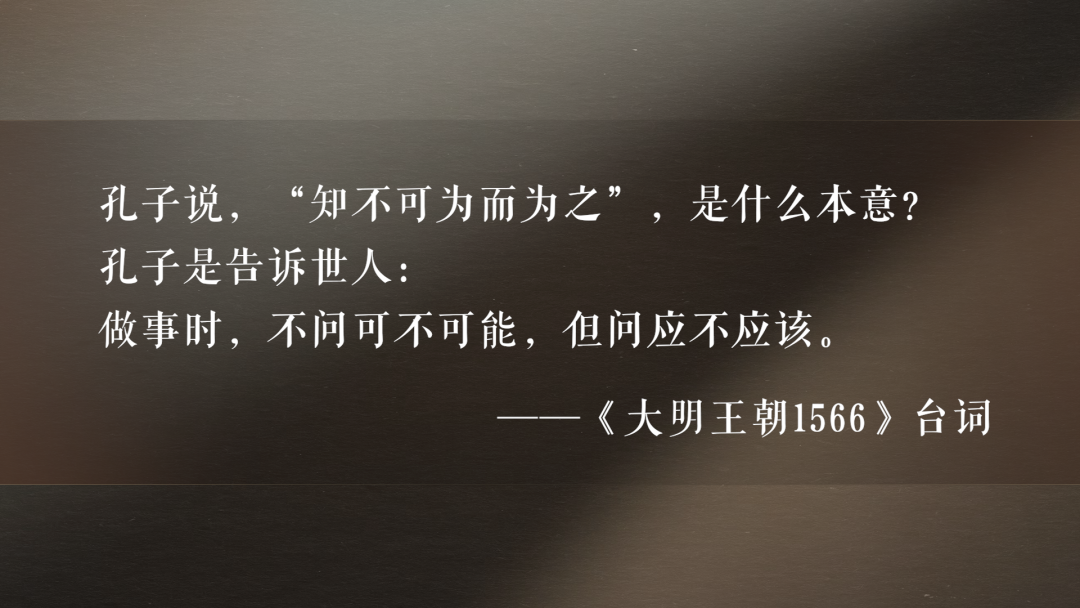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宋)王曾撰,张其凡点校:《王文正公笔录》,中华书局,2017年。
(宋)王素撰,张其凡等点校:《王文正公遗事》,中华书局,2017年。
(宋)沈括撰,金良年点校:《梦溪笔谈》,中华书局,2015年。
(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
(清)吴永口述,(清)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美]柏文莉著,刘云军译:《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
[日]岸见一郎等著,渠海霞译:《被讨厌的勇气》,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
王瑞来:《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中华书局,2010年。
徐红:《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进士——以精英分子为中心》,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王善军:《宋代三槐王氏家族的仕宦、婚姻与文化成就》,《河北学刊》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