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写完回头看,这篇文本应该并不那么易读的,毕竟这本身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也正因如此,我尝试分辨了很多概念,到头来显得有些外部、太过理智,根本也违背了“复活感觉”的目的。所以,这只能被视作是一份暂时的笔记,一次总结归纳。如果可以,我尽可能想将其中说到的种种付诸实践。
——
 buzaichang.xyz
buzaichang.xyz
首先还是应当问,“不在场”到底是什么样的节目?它想要回答什么问题?
尽管“不在场”的节目没什么明确的主线,但,仔细听下来,你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若隐若现的联系。除了重轻老师的个人魅力以外,材料的枚举、结构的组织、结论的提出,都共同组成了一种风格,一种结构,它们牵引着质料——乐句、旋律以及它们背后那些人的故事,不断地盘旋、环绕,标识出圆心所在的问题,那是“不在场”最关心的问题。
有一组相互印证的线索,可以提示。首先是“不在场”的“自我介绍”:
不在场是一个音乐话题为主的播客,我在这里与你分享,自己对各种无用之事的obsessions。 现在中文互联网里充满结论。各种论断,总结,模式,规律,力图揭示一个本质--对抗这「干货」的气氛,是不在场的初衷。 我们的障碍从来都不在“理解",而首先在感觉。缺乏感觉基础的闲谈往往只是相互愚弄的把戏,令人厌倦。我只希望这个播客能符合如下描述:它内容最季碎、逻辑最不严密、立场最模糊、取材最缺乏代表性、摘不出任何takeaway,从而做到另一种“听了和没听一样”,无聊得耳目一新。让感觉复苏吧!希望这个不在场,最终可以回到在场。
其次是“不在场”的第一封邮件,你可以通过竹白给重轻打钱,来订阅,以看到,其中有一段:
……于是我开始设想一些小的视角,小的点,回归到基本的感觉。听音乐的感觉。 长期以来我把自己艺术体验方面的麻木归结于成长,比如荷尔蒙水平的下降和对世界的熟悉。然而在一个15秒视频保证让你笑到地上,并且持续三个小时不停的高强度娱乐的当下,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仍然受到缺乏感觉的困扰,感觉,任何感觉,都如同黑洞一般缺乏着,这就不是简单的「成长的自然变化」可以概括的了。 翻转电台的小李老师说时代的症结在自信心。我想我的时代症结就是感觉,感觉的缺乏。让感觉重新降临,不是要回到懵懂的过去,让自己变成少年,而是,(这怎么能说得清楚呢?),面对它,实在地听见它。这如此简单的事情,需要一边克服对「道理」和权威的渴望,一边克服纯粹直觉的沉沦。不是那么容易。 而这个中道必然与历史的视角统合——历史不是僵化的定义堆砌,也没有清晰的概念边界,它是潮湿而混乱的印象森林,钻进去的人再出来,心里有一个隐约的轮廓。当我意识到这俩是同一件事的时候,我就不再纠结了……
“在场性”是一个哲学概念,我也不懂,但无所谓。重轻已经阐述了他理解的“在场”与“不在场”,其中的关键就是“感觉”。这个“感觉”,是无法用两种方法得到的:第一种是“理解”,对于“道理”和权威的渴望,僵化的定义堆砌及清晰的概念边界;第二种是纯粹直觉的沉沦,是一头钻进潮湿而混乱的印象森林,不再出来。
第二种是好理解的,就是不理解、不拷问、不反思,完全相信自己的知觉,沉迷感官刺激,而不去“矫情”,不去考究“为什么我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将所有的愉快情绪都看成是享乐,将享乐全部看做单纯的享乐,认为情绪没有维度,它不需要故事和道理,它只有不断地循环、沉沦,充满强迫性而空虚不已。当然,这一侧显然不太能困扰我们,至少如果我们已经成为“不在场”的听众,势必已经对于“思考”本身的价值有了一定认识,不会轻贱分析的行为。
所以重要的是如何处理第一种情况,也就是对于“理解”的盲目相信,对于“道理”和权威的渴望,依仗僵化的定义堆砌及清晰的概念边界来处理所有问题。
科学实在论是一种当下大行其道的价值观,或者说,经过了启蒙的大部分人都具备了一种实证的倾向——不管任何事情,我们都需要一种确凿的解释,需要数据、知识、理论,来让我们明白、理解。
在这种价值观统治下,当问到“为什么我们会喜欢听音乐?”时,我们会更倾向于这种答案:从脑神经科学角度讲,音乐可以激活我XXX脑区,促使XXX腺体开始工作,分泌XXX激素,使得我们产生愉快的感觉。或者,从人类历史和行为的角度说,音乐与人们的劳动、生活息息相关,从XXX时代开始就是如此,XXX伴随着人类的演进,具有XXX和XXX的特征,有XXX和XXX作为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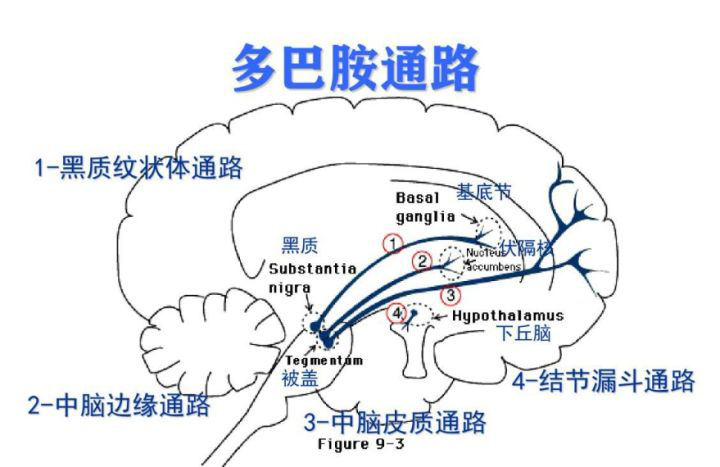
“只是相互愚弄的把戏,令人厌倦。”这种说明式的论据陈列,“理性”推导,与其说是在说服别人,不如说是在说服自己,与自己的感受做对错的辩论。并且这种“对错之分”多半是外在的,要想尽办法撇掉主观的成分,寻找某种虚假的客观中立立场,希望把道理变成数学题、化学等式那样的计算、配比。
从中,我们能够得到某种“完美”的答案,某种意义上的“完美”,即是说,这个答案是确凿的、结构稳定的、条理清晰的,它符合某些人对于答案的要求和想象,像是某种优雅的科学仪器,或者说是美丽的工具,棱角分明、冷酷专业,并且绝对自洽、符合原理,甚至可以用一种恋物式的目光加以审视。
而现代意义上的所谓“学习”“成长”,大部分时间无非也就变成了工具的囤积,数据分析、思维导图、拆书法、图像记录……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帮助人们玩起了归纳演绎的游戏,以一种绕远路式的反直觉方式,让当事人有了一些获得感,并误以为自己获得了启示,误以为自己这波操作淋漓尽致。
对此,虽然很想聊休谟问题、能指链之类的,但,它们本身也是一种“理解”,难以用几句话说清。面对这个问题,倒不如用一些感性的方式,有一段话以前看过一直很喜欢,但现在已经找不到,只记得大概可以表述如下:
具体的痛苦是几乎无法描述的,用数据、用事实都不行,那些干瘪的说明不足以形容当事人感受的万分之一。我们能做的是搜肠刮肚、穷尽修辞,让自己的文字像粉末一般洒在痛苦的边缘上,拼命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以展示它朦胧的形象。
作为补充说明,引用一下维特根斯坦的名句:
我们踏上了光滑的冰面,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我们也正因此无法前行。我们要前行,所以我们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
这甚至可以说是某种反对“纯然理性”的视角,在于上文提及的“完美答案”,其致命的缺陷反而在于“完美”。因为这里的完美意味着完全脱敏,和谁都没有关系。犹如光滑的冰面,拒绝所有的摩擦。
而消除摩擦的办法无非是对自己进行削减,让一切都处在基本可控的范围内。就像从工具铺里买回来的锤子,锤子作为工具是优美的,用钢铁和聚合物制成,用材扎实、轮廓干练,是完美的敲打工具,却也只能用来敲打,干不了别的事情。

更进一步说,有意思的是,锤子所处理的敲打需求,多半也是人自己创造的,敲打钉子、敲打钢铁、敲打砖石,工具的再生产使其早已远离了自然状态,而总是高居现代工业大厦之中,有自己的位置,远离大地。同理,各种学科大厦,总是建立在一些构架之上,当我们援引一个理论时,总是会带入某些经常被省略的前置条件而不自知,从而造成短路。以至于,当我们欣赏某些理论的优雅时,其实欣赏的还是幻觉。沿用上面的例子来说,之所以锤子那么好看、好用,是因为我们还发明了钢铁、聚合物以及钉子,它的便利、干练是有条件的。
那么倘若我们想要追溯“锤子”的成功史,仅仅聚焦锤子本身的发展,那些关键人、关键事,几乎是不够的。有可能的话,我们应当回顾整个技术的发展史,俯瞰整个技术革新的发展,今天一瞬凝结了百载的变迁。以这种视角,我们才可以更好地洞悉工具优雅的秘密。
这点在人文领域,无疑是加倍的。正如上文所举的例子,具体的痛苦是千万种,但“痛苦”二字所有人写出来都是一个模样。我们可以痴迷于“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表达形式,但这个形式是必须放在辛弃疾老师的遭遇背景下,才能绽放出悲怆的生命力的。这可以用来回答,为什么文青的复读总归是无效的。

因为“复读”仅仅是对于形式无效的挪用,而丢失了原本的情景,遗失了“感觉”。你不能因为喜欢锤子,就尝试用锤子解决所有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障碍从来都不在‘理解’,而首先在感觉。缺乏感觉基础的闲谈往往只是相互愚弄的把戏,令人厌倦。”
即便一个人拥有最完美、最完备的知识,他依然必须面对犹如泥淖般的现实生活,知识必须经过人的中介,经由人的双手去影响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知识不过是工具、是参考。而,面对生活中潮湿而混乱的印象森林,地图无法标识出每一棵树的位置,罗盘所指示的不过是大概的方位,从知识到现实总是有或长或短的距离,最后负责辨识道路的还是人自己,在每一个岔路口做出决定的还是人自己。
问题是,此时做出决定的依据是什么?如果知识只是一种参考,那最终主导这个过程的力量是什么?我要说,这就是“感觉”,一种不那么确凿的、神秘的东西,只能在具体情况中讨论,在大量的经历中积累。我们应当了解到,我们都是凭“感觉”在做事的。
而对于“感觉”的运用,是一种关切,去过问每一个人、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时刻、每一件事情。正如,每一种痛苦背后都有它们具体的遭遇,是生死别离、是壮志未酬、是力有不逮,它们寓于一个个故事中、寄宿在一个个情景里,里面除了数据和事实,还有情绪的抒发、价值的判断和理念的贯彻,它们比“锤子”更加深邃,比“天凉”更加彻骨,它们只属于“在场”的人。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不在场”的我们,如何去复现那种不可说的“在场”的状态?
至少我们已经知道了,那种套模板、抄答案的行为,依靠平铺直叙,是做不到的。正如,“不在场”第一季最后一集提到的,这是一场“开采/挖掘”,有大量的前期探测工作,而我们得到的从来不是确切的答案,只是围绕我们目标搜集各种征兆、特征,蛛丝马迹,去推断宝藏的位置,去推测、想象那个冬天小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最终的答案永远只属于真的撸起袖子去挖掘的人,宝藏属于他们。
而,分享它又是一项艰苦卓绝的挑战,只能披肝沥胆、奋力一搏。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终极的关切点上不断盘旋,刮起旋风,将一切相关的东西都席卷进来,最后才能用风眼去彰显它的形象。或者说,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圆心,我们就不可以直接点一个点,说它是圆心,我们只能通过画一个圆,才能间接地标识出圆心所在位置。
我们应当意识到语言的孱弱、知识的无能、形式的空洞,如果我们要去到一个无法直接去到的地方,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另辟蹊径,希望用一种曲折的、迂回的、零碎的、模糊的、无用的手段去触及。为此我们要去苦心孤诣地寻觅、捕捉,那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又曲径通幽的东西:平凡故事里的龃龉、美国模糊的面孔、雪国小屋里降临的女神……
还记得,在某期节目的小宇宙评论区里,重轻老师写过一个回答。因为节目下线,已然不可找到,我只是仍然记得那句话的大致意思:
一个伟大作品的诞生,要求一份的灵感和九分的坚苦卓绝。事后,灵感已然不可考,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考察这九分的坚苦卓绝。
在我理解,这段话并未说完,它还有隐含的后半段:
这一份的‘灵感’就是我们所说的‘感觉’,它神圣而神秘,不可直接言说,它依靠九分的‘坚苦卓绝’被赋予肉体,降生于世。 也因此,在九分的‘坚苦卓绝’中,暗藏着线索,汗水、血液,妊娠留下的纹路,通过它们,我们可能复现出那时产房的情景,回到在场的状态,让感觉重新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