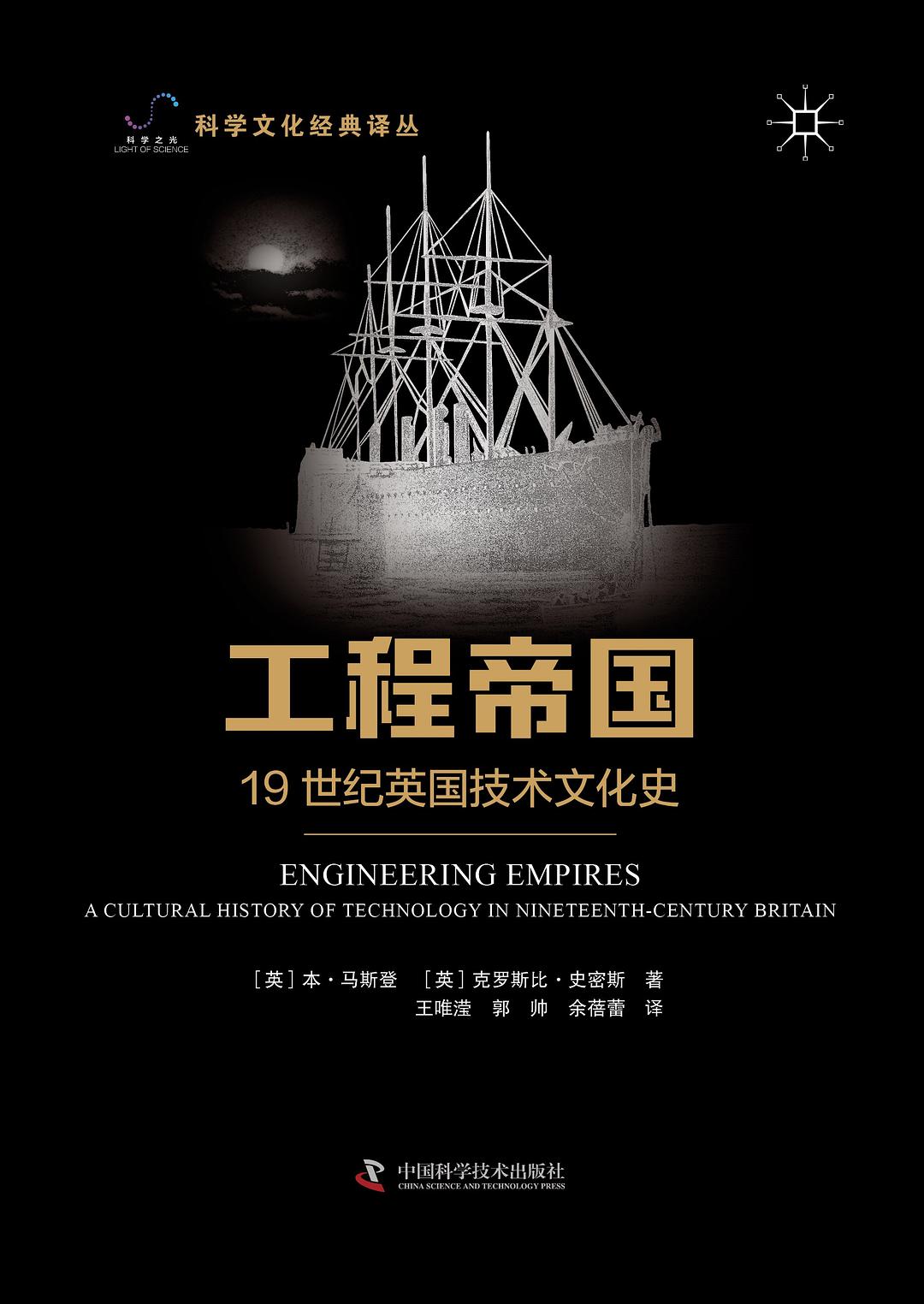在整个19世纪,瓦特和蒸汽机逐渐成了视觉图像、实物演示和文字的宣传热点,甚至连印刷商都广泛宣传他生前的6幅肖像画[创作于1793—1815年,作者之一包括艺术家亨利·雷伯恩爵士(SirHenryRaeburn)]。此外,与瓦特的发明相关的画像也被广泛传播,就像牛顿与苹果的画像一样经典。例如,R.W.巴斯(R.W.Buss)的一幅作品反映了对瓦特的想象:年轻时的瓦特在消磨时间时凝视着茶壶,旁边有一位并不赞成他的年长女性注视着他。一些维多利亚时期的画像,如詹姆斯·E.兰德(James E.Lander)的《瓦特与蒸汽机》(Watt and the Steam Engine)也塑造了类似的形象,或者描绘瓦特20多岁时在工作室里努力研究格拉斯哥学院的纽科门模型时的样子。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正值明治时期的日本,一幅关于瓦特“发现”了分离式冷凝器的原理的印刷版画风靡于日本的各大学校,用于激励年轻的日本企业家,显然这幅作品的影响力颇为广泛。

瓦特与蒸汽机
由弗朗西斯·钱特里(Francis Chantrey)爵士制作的瓦特半身像,更是充斥于科学与工程领域各种具有纪念性的场景。小詹姆斯·瓦特积极推动父亲的半身像在伦敦皇家学会顺利展出,另一尊瓦特半身像则被送到了法国巴黎科学院。为了纪念瓦特,小詹姆斯还在位于汉兹沃思的家中铸造了一座雕像,并在格拉斯哥大学树立了另一座雕像。格里诺克的居民也自发地订购了瓦特雕像,将其放置于瓦特捐赠的图书馆里。公众募捐的资金促成了一座宏伟的坐姿雕像的安置,该雕像由钱特里制作的半身像扩建而成,其复制品成了瓦特纪念馆的一部分(带有布鲁厄姆的题词),进入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安置于格拉斯哥毗邻商业区的乔治广场,也传播至利兹等富裕的蒸汽动力纺织品生产中心,尽管其过程颇具争议。
在早期铁路建造者的内部叙事中,或电报界主要人物发行的小册子里,瓦特的朋友及赞助商们书写并影响着关于蒸汽机及其所谓发明者的早期舆论,从而确保了“瓦特发明”的主导地位。在这一时期,人们对动力的崇拜与日俱增,对于“机械”或“装置”抱有矛盾性心理,一方面它是国家财富的来源,另一方面又象征着一种精神破产,意味着“蒸汽”和“瓦特”被赋予了诸多不同的价值。
蒸汽史学发展于极端反标签主义的环境中。瓦特在1796年写了《一个简单的故事》(A Plain Story),概述了蒸汽机的起源,瓦特最初将书稿提交给了专利律师。1797年,爱丁堡的《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收录了作为瓦特主要盟友之一的约翰·罗比森有关“蒸汽”和“蒸汽机”的文章,证实了瓦特作为蒸汽革命性改进先驱的重要地位。当理查德·菲利普斯(Richard Phillips)将这篇文章纳入他的著作《公众人物》(Public Characters,1802—1803)时,他向瓦特本人请求批准和修改。正是因为瓦特后来修改了罗比森对“蒸汽”和“蒸汽机”的描述,使其对手们对蒸汽机的贡献被淡化了。在伦尼的敦促下,小詹姆斯·瓦特收集了瓦特的传记素材,并于1823—1824年在麦克维·内皮尔(Macvey Napier)更新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发表了讣告,捍卫了父亲的声誉。即使是约翰·法里(John Farey)于1827年(瓦特去世后)出版的关于蒸汽机的权威著作,也反映了作者对瓦特在世继承人的亏欠。
瓦特于1819年去世,如果说他的离世产生了什么影响,那便是赞美的声音愈发强烈。1824年6月,科学、商业、政治和军事领域的人士聚集一堂,为瓦特的公共纪念碑募捐。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共识,从工匠教育的倡导者到“工业革命”时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纷纷响应。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汉弗莱·戴维爵士赞扬瓦特发展了“高深的科学”,称他的地位比肩阿基米德,并且从他身上看到了“知识实际效用”的典范。瓦特“增强了人类探索外部世界的动力,提升并增加了人类生活的便利和乐趣”。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认为瓦特的发现给他带来了“直接的个人利益”,也为“这个国家的纺织业”(“我们国家财富的来源”)赋予了“新的活力与精神”,瓦特能够获得“热烈的掌声”也就不足为奇。皮尔想立一座纪念碑,作为“人类尊严的普遍证明,因为这些发现使人类变得崇高,它既能使成千上万的人享受舒适生活,又能扩大帝国的疆域、壮大帝国的力量”。后来,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将这些评论提炼成纪念碑文,为最终伫立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纪念碑增添光辉。他评价瓦特道:“他展现了人类智慧的理想;他是物理学研究的先行者;他改良了蒸汽机;武装了人类;使虚弱无力的双手变得力大无穷;他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施恩于全世界。”
除了引发科学、制造业、文明和帝国的变革,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也为战争带来了激动人心的胜利,确保了国家的稳定,抵御了他国的威胁。英国首相利物浦勋爵断言,蒸汽机意味着“军事战役甚至是整场战争的成功”,不再取决于风向。蒸汽机已经成为“推动伟大文明事业的、道德的、难以抗拒的杠杆”,贸易委员会主席赫斯基森(Huskisson)坚称,如果没有瓦特的发明,就不可能维持刚刚结束的对法战争的巨额开支。同样,议员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Sir James Mackintosh)也认为,正是瓦特的发现才“使英国能够经受住她所参与的最艰巨和最危险的冲突”。因此,萨迪·卡诺并非唯一一个将蒸汽力量视为影响英国商业和军事力量核心的人。
社会评论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对瓦特的评价则较为矛盾。他对有关实际效用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在公开赞扬瓦特的大会召开后不久,托马斯·卡莱尔便将这位工程师与马库斯·布鲁图斯(Marcus Brutus)做比较,布鲁图斯自然比索霍区的瓦特品德出众,但“就其效用而言,蒸汽机能让恺撒死上500次”。卡莱尔于1829年在《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发表题为“时代的象征”(Signsoftimes)的文章中写道:“在任何意义上,我们崇拜并追随力量,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物质的追随。”卡莱尔认为他所处的时代“不是一个英雄的、虔诚的、哲学的或道德的时代,而是一个机械至上的时代”。这是一个“机械的时代,无论外在还是内在皆是如此”。“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是直接由手工完成的,一切都是按照规则和精心计算运转的。”手工技艺已被机械所取代,“活生生的工匠们被赶出自己的作坊,从而为速度更快的机械工匠腾出空间”,织布工人的手指被“铁手指”所取代,甚至连船帆和船桨也屈服于机械动力,“人们靠蒸汽横渡海洋,伯明翰的‘火王’号早已造访了‘神话般的东方’”。
卡莱尔含蓄地指责了“火王”号和所有其他“机械时代”的代表,因为它们对人类的神秘、诗意和精神方面的破坏并没有延伸到詹姆斯·瓦特身上。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提到瓦特父子利用“大自然的免费馈赠”,并非通过制度或其他形式的社会机制,在“不起眼的壁橱”和“车间”里同牛顿和开普勒一起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写到“制图主义”,他这样描写瓦特:“手指发黑,眉头紧锁,在他的工作间中寻找火的秘密。”然而,詹姆斯·瓦特卓越的“创造天分”与其发明应用的矛盾性的分野,并没有对19世纪的动力崇拜者造成很大困扰,他们仍自由地推崇瓦特的名字,就像先人们尊崇圣徒一样。事实上,对瓦特生平的主要赞誉并非来自英国,而是法国,体现在巴黎科学院常任理事弗朗索瓦·阿拉戈1834年12月发表的讲话中。阿拉戈在准备这篇“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悼词”的过程中,拜访了索霍工厂,与统计学家詹姆斯·克莱兰(James Cleland)博士一起参观了格拉斯哥港,意外地发现那里的瓦特纪念碑并没有建在瓦特开展实验的房子里(已不幸被拆除),而是建在了当时正在作业的蒸汽机边。阿拉戈除了与瓦特的熟人和朋友们交谈,还经常与小詹姆斯·瓦特通信,两人在巴黎面对面地探讨了悼词文稿。
1834年秋天,阿拉戈向瓦特的亲友打听他们“熟悉的瓦特的轶事”,来“说明瓦特早期的天赋”,他们欣然提供了一手资料。小詹姆斯·瓦特转述了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信中讲的故事,是由简·坎贝尔(Jane Campbell)告诉吉布森的,而这些故事又是从简的姑妈玛丽昂·坎贝尔(Marion Campbell)处听来的。作为瓦特童年的朋友,玛丽昂在他们相识50年后写下了这段故事。在其叙述中,瓦特是一个擅长讲搞笑故事的孩童,也是一个崭露头角的问题解决者。他可以用数学计算出炉膛和墙壁所占的面积。当然,这个故事并“没有完全”复述玛丽昂·坎贝尔所说的,“不过事实是一样的”,瓦特“关于蒸汽的力量与弹性的最初想法”,可以追溯到一个无聊的孩子看着蒸汽从沸腾的茶壶中冒出并凝结在一块组合板上。后来,小詹姆斯·瓦特要求阿拉戈放弃吉布森信中的修饰,而是采用玛丽昂的原始口述文本。这样一来,阿拉戈的叙述中加入了水壶,但限制了其与发明的联系。
事实上,阿拉戈笔下的瓦特也并非完美无缺,他曾在18世纪60年代屈服于“资本家愚蠢的短视”,放弃了研制运河工程的发动机,差点使人类错失蒸汽带来的好处。显然,是他的妻子从“疲惫、灰心和厌世”中拯救了一个公认只有两种爱好的人。否则,瓦特的生活将会乏味沉闷到需要向习惯了丰富多彩内容的听众道歉。相反,他的生活则充斥着辛勤劳动、“极其细致的实验”研究,以及沉思,而且“坦率”“简单”“向往正义”和“不竭的仁慈”是装点瓦特形象的“调味剂”。
当瓦特与那些代表“利益集团”、古老传统的“顽固派”和对国家或个人荣誉故作骄矜的“嫉妒者”做斗争时,他需要采取严厉行动的意识才被彻底唤醒。在阿拉戈看来,瓦特并不是萨弗里的传承者。被矿主们无视的萨弗里只能将发明应用于乡间别墅和花园,瓦特是不幸被忽视的法国民族英雄帕潘的合法继承人。瓦特的工作证明了那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无名小卒也在蒸汽机诞生和将“英国国家权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不仅仅是勋爵人家的专属,尽管瓦特因“出身”寒微而错失了贵族身份。
阿拉戈塑造了瓦特“物理学家”的形象,就像瓦特自己所做的那样,他把这种声誉当作商业成功的关键。作为爱丁堡皇家学会(1784年)和伦敦皇家学会(1785年)的会员,瓦特使用一枚刻有眼睛图案和“观察”二字的印章,强调他随时准备改进所看到的一切,成为像亚当·斯密一样的“观察家”。阿拉戈将瓦特列于物理学领域蒸汽机改进阶梯的顶端,视瓦特的成就高于英雄亚历山大。这位初出茅庐的物理学家童年时对水壶的观察表明,他和牛顿一样,通过“持续不断的思考”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他对水的复合性质的清晰陈述,与牛顿在光学研究中对实验事实同样深刻且无可争议的阐释一脉相承。他也像培根一样,总是用事实来武装自己,他既是一个学习者,也是一个观察者。他的工作室不是鲜有人至的楼阁,在“某种程度上像个学院”,向所有人开放。人们可以在那里讨论艺术、科学和文学的所有问题。
阿拉戈声称走遍了英国,走访了一百多个不同阶层和政治派别的人,询问他们如何看待“瓦特对英国的财富、权力和繁荣所产生的影响”。他得到的回答与1824年6月的演讲相呼应,人们纷纷强调瓦特在抵御外敌从而维护英国的“独立和民族自由”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爱国作用。瓦特的仁爱并非直接体现在参与军事行动上,而是通过他的发明在战争背后的财富积累方面发挥作用。阿拉戈还指出,自亚历山大大帝起,军事指挥官们更为尊崇的是思想。小詹姆斯·瓦特提供了从索霍区和其他地方售出的发动机数量的数据,从而使人们能够进一步具象化地了解他在维护国家繁荣方面做出的贡献。这些数据同样证明了瓦特非凡的创造力和管理能力:
他是600万乃至800万劳动岗位的创造者。这些劳动者勤奋刻苦、不屈不挠,无须权威来镇压骚乱,而且他们每天的劳动报酬仅为半便士。瓦特凭借他杰出的发明,为英国提供了开展激烈战争的支持手段,否则在这场斗争中,她的民族性将岌岌可危。
阿拉戈所描绘的瓦特的形象是如此辉煌、鲜明,以至于他认为有必要对那些比卡莱尔更激进的人做出回应。那些人坚称瓦特的发明是“邪恶的工具”,会导致“社会灾难”,认为机械只是将“繁荣”集中在资本家手中,而它带来的好处能否超越“工人阶级”被剥夺工作、休闲和自主权?阿拉戈以几何学为灵感进行了归谬法论证,从经常重复的“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实验”中得出总结,回应了那些1830年在英国高呼“打倒机器”的言论。对阿拉戈来说,以蒸汽为动力的机械是一种可以促进平等的巨大力量,给穷人带来了迄今为止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到的福利。阿拉戈看到瓦特蒸汽机帮助人们“深入地下”,清理“宽敞的长廊”,获得“取之不尽的矿物财富”;将固定海上船只的“巨型电缆”和“透气的、带有花边的纱布”拧成一团;排干沼泽灌溉焦土;使以前在瀑布脚下更易获得的电力(指水力发电)出现在了“城镇的中心”。工业集中发展,生产的产品会更便宜,人口会增加,人们将“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如果把蒸汽机安装到船上,它将取代三到四倍的划船的人力并发挥百倍的功效,我们的祖先曾把最繁重的船上劳动作为对最严重的罪犯应受的惩罚之一。在几蒲式耳煤炭的帮助下,人类可以克服各种障碍,使平静、逆风,甚至风暴中的航行都变得轻盈。蒸汽机在铁路上疾驰,比最好的赛马还要迅速,况且赛马只能载着单个骑者,而蒸汽机要承载成千上万的旅客。
阿拉戈以更加热切的宣言结束了他的演讲:“我将毫不犹豫地宣告我的信念,当蒸汽机已为我们提供了无尽的服务并且实现了它承载的所有奇迹时,人们应满怀感激地谈论这个属于帕潘和瓦特的时代和他们的伟大成就。”
(本文选摘自《工程帝国:19世纪英国技术文化史》,[英]本·马斯登、[英]克罗斯比·史密斯著,王唯滢、郭帅、余蓓蕾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