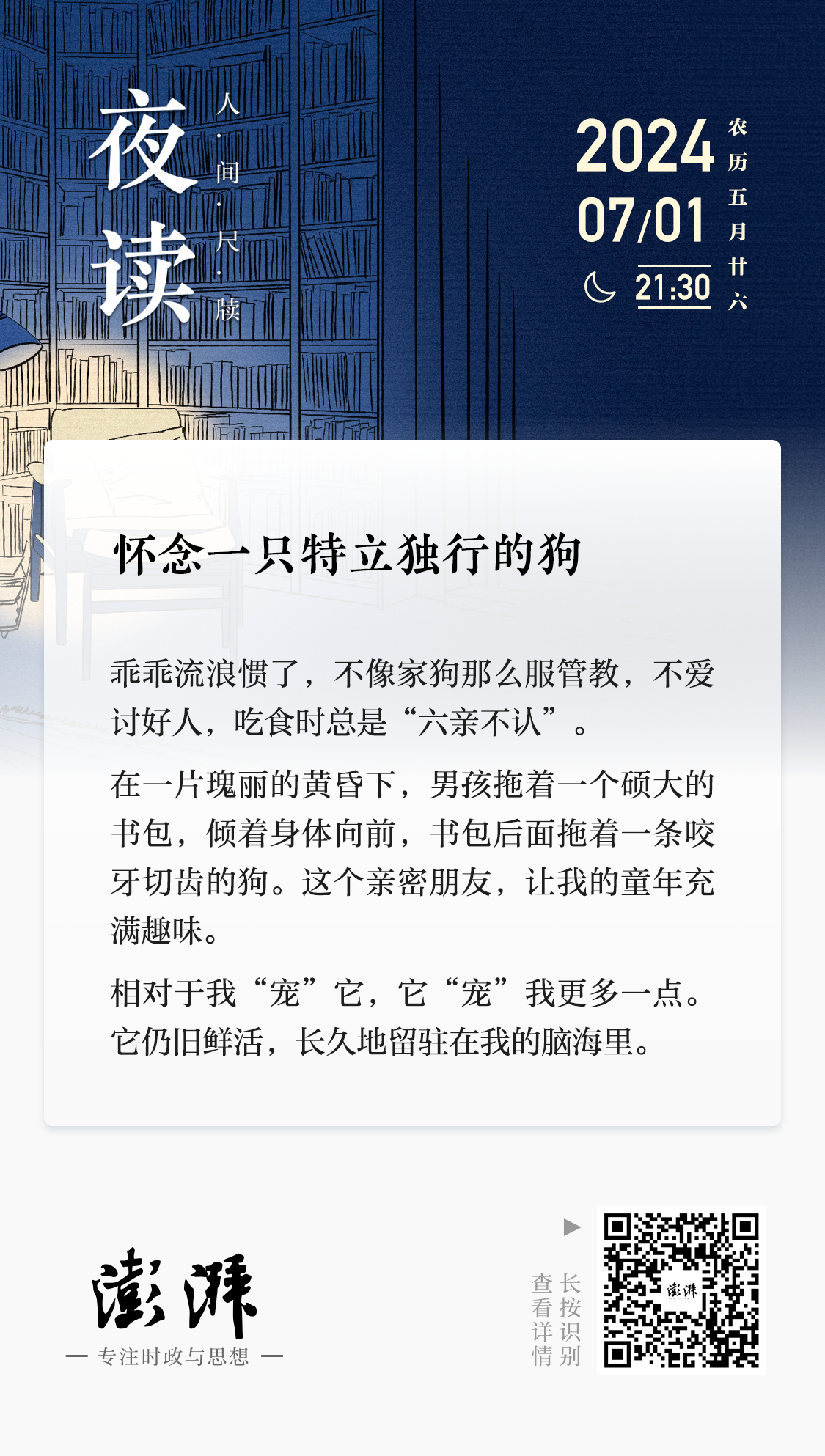三十年前的一个冬天,一只脏兮兮的小白狗突然出现在我家的门洞里。它冻得哆嗦,我妈看它可怜,丢给它一盆剩饭。我和姐姐蹲在地上,远远地看它。它个头不大,但护食的样子着实吓人——半俯着上半身,后腿紧绷着,整个头都没入盆里,叼食力道之大撞得不锈钢盆咣咣直响,嘴里还不断发出“呜呜呜”的警示。
之后每隔几天,它就会出现在我家的门洞,我们扔一些吃的给它。时日一长,它留了下来,和我也日渐亲近。
我想让它听话一点,给它起名叫“乖乖”。事实上乖乖一点都不乖,它流浪惯了,不像自小养大的家狗那么服管教,不爱讨好人,吃食时总是“六亲不认”,还时不时就跑出去好几天,不见“狗影”。
我们也从不拘束它,没给它戴过链子。它来,我们就管吃管住;它走,我们就当它没来过。它更像猫,保持着特立独行,不献媚、不乞食、不看家,也不冲陌生人乱叫。妈妈有时骂它是“傻狗”,它若无其事、吊儿郎当地溜达到一边。就这样,乖乖像一个借宿者,与我们家建立了一种友好但不依赖的关系。
那时我有一个很大的牛仔书包,装得下很多书本和一条狗狗。放学后,闲来无事,我就把乖乖强行装到书包里,背着它玩。它不情愿,扭来扭去,伸出头来舔我的脖颈,有时挣脱出去,追在我屁股后面,忿忿地撕拽我的书包。
于是,在一片瑰丽的黄昏下,比一个男孩背着一条小狗更治愈的一幕出现了:男孩拖着一个硕大的书包,倾着身体向前,书包后面拖着一条咬牙切齿的狗。回想起这个场景,我不禁嗤笑。这个儿童时代的亲密朋友,当真是让我的童年充满趣味。
记忆中,乖乖从不在放学的路上等我,也不会为口吃食冲我乞首摇尾,反倒是我每天要缠着它。有时它“外出”几天,我就格外失落,毫无玩耍的兴致。
我之所以愿意和它玩,是因为乖乖懂得“捧场”。当我拿着一根木棍儿当宝剑,幻想自己是武林高手,在院子里招猫逗狗、撵鸡揍鹅时,只有乖乖最为配合,在我左右欢脱地蹦,而其他小动物只会四处逃窜。
有时我们玩嗨了,就钻到棉花地里疯跑,广阔的田野很适合它的秉性。乖乖跑起来带风,跑到哪里就把哪里的棉花叶搅得哗哗响。它耐力也极好,一口气能跑出去很远。听不到它的动静时,我就大喊一声“乖乖”,它立马又搅起一片哗哗声,冲刺回来。
三十年后,透过记忆之窗,我在这条成熟的小狗身上,竟看到了一种坚定的温柔。这种温柔不是源于忠实,因为我知道乖乖并不忠于我,它似乎深深怀念着另一个主人,因而经常离家;也不是源于“通人性”,因为小时候的我有些憨鲁,非要说它能通我的心意着实有些牵强。细细体会的话,这种感觉倒像是一个年龄偏大一点的朋友对我的关照。
人们习惯把自己养的小动物叫做“宠物”,这个词放在乖乖身上有些别扭,因为相对于我“宠”它,它“宠”我要更多一点。
后来,乖乖葬身在飞驰而过的汽车车轮下,像一团白雪,融化在了漫漫岁月里,也在我家人的记忆里变淡。唯独于我,它仍旧鲜活,似我童年的注脚一般,长久地留驻在我的脑海里,在我身处繁华都市却感到内心离索时,给予我宽慰。